德云社總教習
從未離開相聲
被譽為“德云總教習”的高峰,總被人當作老藝人,詢問他從藝多少年了?這讓生性嚴謹的他每次都要耐心地征詢對方:應從哪一個節點,算作從藝起始年呢?
在天津德云社后臺,高峰接受記者專訪,談到最初與相聲結緣的故事:“從首次登臺的時間計為正式從業的起點,那我就真不算早,我是在初中二年級時登臺表演相聲的。”他又笑著反問:“比如有的人一提就是將半輩子獻給了相聲事業,結果中間好幾十年都沒碰過相聲,很可能半輩子加起來也沒正式說過幾年相聲,這也算從藝半生嗎?”
少時自學的高峰,曲藝路因其赤誠的熱愛而通達,博得老先生們的一致認可。他正式拜的師父有兩位,相聲門師從相聲名家范振鈺先生,西河門師從曲藝老藝人金文聲先生。這兩位老先生都對他青睞有加,也都跟郭德綱說過:“我有個徒弟,現在還上著學,有機會讓他去北京說說。”
高峰日日與相聲為伴,感悟日深。他慨嘆老輩藝人對相聲藝術永遠存有恭敬心,他們將藝術觸角伸進生活的各個角落,犀利地剖析著社會的每一個細胞,并于演出之際時有發揮,“一個相聲作品能夠成為經典,就是因為它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得到了觀眾的認可,相聲肌體刻烙的是時代印記。”
當問及今日的相聲創作為何難出經典?高峰反問:“怎麼證明一個相聲作品火了呢?它在社會上能產生轟動效應,能創造流行語言。馬志明先生和謝天順先生的相聲作品《糾紛》中有一句‘你軋我腳了’,因場景設計邏輯準確,故事飽滿,很簡單的一句話,成為多少年的流行語。朋友間有了糾紛,有人來一句‘你軋我腳了’,就能緩解氣氛,可見相聲藝術對生活的影響力。”反觀今日的相聲創作,高峰直抒己見:“現在是把流行詞匯擱在相聲里,相聲由過去的創造流行元素,改為借用已有影響力的流行語,這個區別直接導致相聲的影響力變弱了。觀眾現場反映可能很熱烈,但忘得也快。我師父范振鈺先生與高英培先生的代表作《釣魚》是上世紀50年代的作品,歷經幾十年,至今經久不衰,令人津津樂道,這其中的緣由值得我們從業者深思。”
金文聲先生推薦他去德云社
頭一場表演了《開粥廠》
記者:您在德云社的演出一般都是倒二,這個位置很重要,感受如何?
高峰:觀眾總調侃我們是“郭德綱于謙喝水上廁所的時間”,其實這個調侃是我用了比較長時間的一開門包袱,最早是我在說書時的一個現掛。正常演出需要控制時間,前面的節目,一個短上三五分鐘,四五個節目加一起就是二十幾分鐘,這些時間都得我來補。那些年我給郭老師助演,經常一演就是四五十分鐘,還演過68分鐘。比如郭老師最后一個節目是夜里10點上臺,甭管我幾點登臺,也得撐到點。后來我上臺得戴塊手表,因為表演時間越來越長,不好估計了。不少朋友反映,你站臺上說半天也不入活呢?我不敢入活啊!一入活,我們就下臺了。剩下幾十分鐘咋辦?我還得翻個節目,小段就不能說時間長了,那得多少個小段才能把時間填滿啊!這就尷尬了。我在“倒二”,是郭老師對我的信任,他認為我有這個能力把握好節奏。又有觀眾給我提過,你怎麼說半天都不下臺呢?這我得聲明一下,可真不是我故意占著舞臺不下去,影響大家看郭德綱。我是帶著任務上臺的,要求我幾點完活,我必須得說到點。
記者:您最早認識郭德綱是什麼時候?
高峰:2005年,郭老師和經紀人王海到天津看望金文聲先生,金先生說:“你先別走,我叫來一個孩子,給你看一看。”那時候我還在讀大學,正在實驗室做實驗,電話沒有信號,金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撥號。等到晚上10點多,我出了實驗室,立馬接到電話:“郭先生在家里等你了,我給你打了半天的電話也聯系不上,可急壞我了!”我急忙忙打車趕去了金先生家。見到郭老師,隨意聊聊天,問我在哪兒演出、和誰搭檔、演啥節目等。最后郭先生說:“行!既然金先生強烈推薦,周末你到北京,周六看一場,周日演一場。咱們互相考察考察,演一場給你50塊錢買冰棍。”人家說考察我那是客氣,那時候一場50塊錢不少了。
記者:到德云社第一次演出效果怎麼樣?
高峰:2005年7月10日,第一次到德云社,我報的是《開粥廠》。按說頭回演出沒有演這個的,難度太大。郭老師一聽說“行”,安排了李文山先生給我做搭檔。演出時,他還安排我返場演了快板《小寡婦》,目的是增強觀眾對我的熟悉度。也是得到了觀眾和郭老師的認可吧。自第一次演出后,郭老師每周都親自通知我周末演哪場。那年德云社還沒火,一場演出大概有六七個節目,算上主持人約有十幾個人,票價20塊錢,刨去人員吃喝穿戴、勞務費、房租水電費等,根本剩不下多少錢,不少時候都是賠錢演出,貴在郭老師對藝術認真,不計得失地堅持。
記者:當時您是天津北京來回跑嗎?
高峰:經常坐火車去北京。郭老師不僅給我勞務費,還報銷我京津往返的火車票錢。有人說,你上學說相聲就為了掙零花錢,實話實說還真不是,路上來回太折騰了,基本上是賠錢圓夢。有家里給的生活費,也不指望著靠說相聲生活,純粹就是對相聲藝術的一腔熱忱。若不是真愛,也不可能從小時候就始終親近相聲。總的來說,當時為相聲支出的錢,遠遠多于掙到的錢。
難忘中國大戲院專場
親歷德云社成長發展
記者:當年郭德綱第一次在中國大戲院辦專場,應該是您最難忘的一次演出吧?
高峰:那是2005年11月5日,在天津中國大戲院。原定是當年10月5日演出,后因故改到了11月5日。那是郭老師第一次離開北京辦專場,也是第一次在家鄉辦專場,很是重視,但確實沒啥經驗。網上總有人說我是救場去的,郭老師因為感動,特別招我進德云社,其實不是。那時我已在德云社演出四個多月了,當天我正好在天津演出,所以人在天津。下午4點多,郭老師的經紀人王海給我打電話,讓我速速趕到后臺。我到了中國大戲院才知道,因為大霧高速公路封了,其他演員還在北京,只能臨時買火車票,到天津站的時間是晚上7點35分,趕到中國大戲院最快也得晚上8點,但專場演出的開場時間是晚上7點15分。我們跟戲院的人商量,可否晚點兒開場?人家不同意,票上印著幾點開始,就必須準點開燈開幕。這可要了命,整個后臺只有郭老師和我兩個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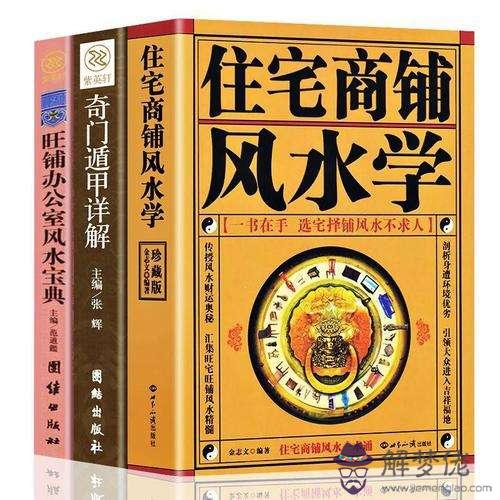
記者:這種緊張的氛圍還真挺有戲劇性的,說起來像傳奇故事,但其實是真事。
高峰:郭老師問我知道《西征夢》嗎?我還真沒仔細聽過。他說,“直接上吧。”我倆換上大褂就上臺了。我們倆都是天津人,在家鄉演出很親近,觀眾對郭老師的包袱很認可,我再砸幾個現掛,效果還挺不錯。結尾的時候,郭老師直接就結束了,我還按照老規律說著呢,他一鞠躬告訴我“到底了”,我說我也鞠躬。這活是愣上,現在叫“盲捧”,按流行語說Bug挺多。很多觀眾對這場演出挺難忘的,畢竟難得有一場演出是沒對過詞的。
這段說完后,郭老師返了《口吐蓮花》,也是大段。說到快一半的時候,我往臺口一看,大伙兒都到了,于謙老師穿好大褂在后臺口等著了。其實不用都穿上,估摸于老師也急壞了,所以穿戴齊全,等招呼。郭老師一回頭看到于老師,心里踏實了,節目也算開開了。演員們都挺不容易的,大伙兒著急忙慌地趕到劇場,氣都沒喘勻就得上臺,這就得業務非常扎實,不然容易忙里出亂。
記者:您是德云社的老隊員了,是怎麼做到一直堅守這個陣地的?
高峰:我是一個隨心隨性隨緣的人,家里人不反對我在德云社說相聲,我在德云社待著也挺自由的,雖然收入不穩定,但一群熱愛曲藝的人聚在一起挺舒服。郭老師火了以后,我們劇場多了,演出場次多了,收入也提高了,這是很好的事情,就一直很安心地待下去了。
說相聲要有師父指導
更需要自身鉆研和苦練
記者:您怎麼評價郭德綱的相聲?
高峰:郭老師的相聲既不是傳統相聲的照搬,也不是嶄新段子博眼球,而是傳統翻新的相聲。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傳統相聲全部創新,觀眾聽著沒有距離感,既親近又新鮮還很有意思。我敢說像郭老師這樣具有轟動效應的曲藝表演藝術家,很難再有了。除了社會影響,他對相聲行業的貢獻是能夠與前輩領軍人物并談的。這個訪談發出去后,我想肯定有評論會講,“你在郭德綱那兒干,當然得說他好話。”絕不是這個概念,我是因為郭老師的好,才會跟著他干。
記者:您被稱為“德云社總教習”,談談這個名號是怎麼來的。
高峰:大概是在2007年,第一批鶴字科招進來后,我和幾個老師一起教學。好幾個老師教,總得有個責任老師,我就是責任老師。“德云社總教習”的名頭是郭老師給起的。前些年,我有個專場,演出得有個名目啊,郭老師就給我想了這麼一個名頭。其實,我是愧不敢當,為啥呢?因為我只是把沒進門的學員領進門來,僅此而已。這不是謙虛,我們這行從來都是老先生們今兒他教你幾句,明兒他教你幾句,甚至有時候是老先生教別人,我在旁邊聽著也等于教我了。這行自古就這樣,只要老先生不支你出去,你就可以旁聽受教。有時候,我假裝擦桌子掃地疊大褂,就為了聽幾句好受教。過去沒有錄像,學員是帶著飯到演出現場,一邊聽一邊記。馬志明先生當年也是帶飯去聽活,除了活本身,還得聽不同人的不同演法。相聲這行,總的來說,有師父的指導,更需要自身的努力鉆研和苦練。有無數段相聲,我一聽就能對口型,這就是聽得太多了。熟能生巧,首先得熟!師父領進門后,一個演員的藝術水準和業務能力的高低,在于個人的自我要求與積累,所謂“修行在個人”。
高峰自述
上初中時登臺說相聲
感謝老先生無私傳授
相聲老藝術家馮寶華和我奶奶家是鄰居,按街坊鄰里輩分論,我稱呼他二爺爺。那個大院里住的人家,幾乎都是干曲藝行的,我特別愛去二爺爺那兒聽他聊天。老先生能耐很大,也特別和藹。我記得一到晚上六七點鐘,他提個包就出門了。現在回想,估計他是到哪兒演出去了。可惜我那時候才五六歲,沒有機會和二爺爺學習相聲。
自初中起上臺說相聲,我登上了不少學校的舞臺。漸漸地,校園的大小活動中,我的相聲成為必備節目,被老師推薦到社會活動中參加演出。在一次慰問老紅軍的活動中,我演了《大保鏢》,老紅軍們靜靜地聽著。我們那時根本不懂看場合選活,用行話說就是“把點開活”,可能說得也不利索,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是特別感謝那些老紅軍對我們學生的愛護和尊重。
沒有師父交代幫襯,我走過一些崎嶇的道路。守著一臺收錄機,挨個兒臺輪著聽,只要是聽到播出相聲,就趕緊錄音保存。同學們知道我的愛好,以實際行動支持我,把不聽的英語磁帶全部贈送給我。我是一邊錄,一邊聽,一邊學。如今我仍然保留著這些已經被時代淘汰的磁帶,大概有近700盤。甭管電腦里存著的相聲段子播放效果有多好,我也沒舍棄這些磁帶,它們是我青春的記憶,也是我當初努力的見證。
別看我從初中開始登臺說相聲,但真不知道社會上還有相聲劇場演出。高考結束后,我在家翻報紙,看到中華曲苑成立兩周年,才知道有相聲專場演出。2001年暑假,我帶著和我一起說相聲的同學一起到劇場聽相聲。中華曲苑門票是10塊錢,包廂是15塊錢,燕樂劇場是6塊錢,名流茶館是10塊錢。后來我才知道,1998年,于寶林、馮寶華、尹笑聲等老先生們恢復了相聲茶館,當時叫“老藝人相聲隊”。此后我就常去茶館聽相聲,去的次數多了,和老先生們慢慢都認識了。
第一次去老先生家,是李鳴宇帶我拜訪王派快板演員何德利先生。我內心想既是看望老先生,也想跟先生學王派快板。沒具體說怎麼個學法,我一個窮學生也沒啥錢買禮物。老先生非常無私,不要學費,讓我周末到家里學快板。后來就約定俗成為周末上午進家學習。何德利先生是出了名的誠懇、樸實、熱情。何先生給我說活,手把手地示范拿板的拿法。我特別感謝何先生,無私傳授不計名利。
相聲門戶中,我的恩師是范振鈺先生,師爺是班德貴先生,師祖是馬三立先生。我2004年6月6日拜師范振鈺,賜“應”字。西河門戶,我的恩師是曲藝老藝人金文聲先生(原名金剛,藝名金連瑞),師爺是張起榮先生,師祖是張士權先生。2006年12月20日拜師金連瑞,賜藝名高增禧。快板門戶亦是金文聲先生的弟子,快板藝名高啟明,師爺是王派快板創始人王鳳山先生,師祖是數來寶老藝人海鳳先生。
作者:張一然

來源: 天津日報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279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