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詠嘆調
——唐詩的發展歷程
作者:徐剛(詩人、作家,曾獲魯迅文學獎等)
中國詩歌的長河,兼收并蓄,奔流直下到了唐代。唐詩是中國詩史上空前浩大的匯流,是時代的呼喚,是文學自身求變、厚積薄發的結果。
唐詩之美,美在詞語。唐詩留下了多少獨特的詞語,詩性與神韻,情感倏忽來去的瞬間。
以李白、杜甫為代表的唐代詩人,站在詩歌藝術金字塔的頂端,使漢語言成為了獨美世界的語言。“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這些光大了漢語言文化的偉大詩人,理應被我們永遠銘記。
唐詩源流
唐詩的繁華,既不是歷史的偶然,亦非瞬息之作。唐朝之前,中國詩歌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至少經歷了三次洗禮。《詩經》一也,它是上游,是源頭,有開辟之功,是加工整理中國語言的輝煌開始,新鮮靈動,晶瑩剔透,溫柔敦厚;是中國詩歌初試啼聲的第一個春天。《楚辭》二也,它是中國詩歌長河由北而南的一次奔流,在楚地的廣闊大地上匯集了當地新鮮的、奇崛的神話與想象,屈原之天上人間,芳草美人,朝發蒼梧,夕至縣圃,其想象之光怪陸離,古人所無,時人僅見。陶淵明其三也,歷經兩晉和南北朝的分裂、戰亂,社會思潮的混濁不清,陶淵明自中年后棄仕務農,耕讀自娛,沖淡高潔。他以“勞役”取代“心役”,其樂無窮。《讀〈山海經〉》第一首:“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王國維《人間詞話》:“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我之境也……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樹立耳。”陱淵明,豪杰之士也。
玫瑰曙光
陸時雍《詩鏡總論》評說“初唐四杰”:“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鄭振鐸稱:“沈宋(指沈佺期、宋之問,引者注)時代的到來,蓋在四杰的所作里,已看到其先行程的蹤跡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筆下無離情別愁,寫送別地長安,為蒼茫山野護衛,“城闕輔三秦”也。“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則世代流傳。楊炯《王勃集序》說:“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楊炯恃才傲物,善五言。《從軍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六十八行,以“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開篇,前三十行中,“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已為不朽佳句。結尾是:“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時光,永恒者也;松樹桂花,柔弱而堅強者也;揚雄,自甘貧窮者也。《長安古意》,及駱賓王其時以為絕唱的《帝京篇》,是初唐七言歌行的代表作。駱賓王以歌行體見長,亦作五言。《于易水送人》:“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對“初唐四杰”,杜甫有詩贊曰:“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歌行體因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得以傳承:“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張若虛的詩存世只兩首,另一首為五言《代答閨夢還》。張若虛被稱為唐朝詩人中“最懶的詩人”。他寫風月,寫相思,寫情感,是上承屈原《天問》,下啟李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的詩人。

第六屆中國詩歌節開幕式文藝演出資料圖片
曠野嘯聲
舒蕪稱贊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是“邁向闊大和永恒的詩篇”。其《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舒蕪有解:“詩人登上高山之巔,眺望宇宙,只見白日已在西天熄滅,云海正在動蕩翻騰。孤零零的一條小魚,又怎能得到安寧之處呢?詩人眼中的境界就是這樣闊大,他把一個人比作孤鱗,密切聯系著像云海一樣動蕩翻騰的大宇宙,來觀察他的命運。”陳子昂為初唐作結,韓愈在《薦士》中贊他:“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高蹈,高揚蹈奮者也!
安史之亂是唐代歷史的一條分界。詩人們不得不從繁華中走出來,走向動亂,走向困苦,走向邊關,并且外觀內省:寫什麼?怎樣寫?詩人的眼光由此變得冷峻清醒,并以不安焦慮去觀照現實。是時也,李白、杜甫雙峰凌云。山水詩,戍邊詩,蔚然成風,或清嘯山水間,或呼嘯邊塞風沙,映帶李杜之側而增風光。
山水田園派史稱“王孟”詩派,王維、孟浩然也。王維先是亦官亦隱,寫《終南山》,開唐代宗承陶淵明一派之先聲:“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語近天然,深美閎約。《鹿柴》月照青苔也,《鳥鳴澗》空山鳥鳴也;又《竹里館》對月長嘯也,《山居秋瞑》多搖曳瀟灑之動感:“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孟浩然是盛唐詩人中的另類,他應舉落第后終身不仕,漫游東南,隱居終老。孟浩然是漫游者,詩亦有游走感,《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又:“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淡得不能再淡了,清得不能再清了,一種風景,一樣心情,一幅白描,漂移在詩歌的長河中。孟浩然有的詩尋不著一點琢磨的痕跡,《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李白《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盛唐邊塞詩中最有代表性的詩人是高適和岑參。高適的詩多雄渾悲涼,如《送李侍御赴西安》:“行子對飛蓬,金鞭指鐵驄。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又《別董大》:“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鄭振鐸說岑參是“開天時代,最富有異國情調的詩人”。岑參在唐代邊塞詩人中的獨特性在于,從天寶八年(749)首次戍邊,遠赴龜茲,兩度出塞,漫游西域,足跡與筆觸,直至新疆蔥嶺內外,無邊荒沙,大塊荒野。岑參是當時詩人中走得最遠、最有荒野氣的詩人。岑參善作七言歌行體,如《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同作于輪臺軍中,一樣風格,兩種語言,各有韻味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全詩均以雪為背景,邊塞白雪,春花喻雪,紛紛暮雪。迵然相異的環境,恍若隔世的人生經歷,熱血沸騰的詩人,筆端蘸滿感情的詞語,岑參的詩便突兀于絕域風沙中。殷璠論之為“語奇體峻,意亦造奇”。在盛唐以邊塞詩聞名的,還有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之渙有《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窮天地之大觀也!
雙峰凌霄
現在,我們要仰望盛唐詩歌的兩座極峰:李白與杜甫。從創作而言,李杜分屬不同時期。李白的名作,大多寫于安史之亂前。鄭振鐸寫李白:“他的詩,縱橫馳騁,若天馬行空,無跡可尋;若燕子追逐于水面之上,倏忽東西,不能羈系……如游絲,如落花,輕雋之極,卻不是言之無物;如飛鳥,如流星,自由之極,卻不是沒有軌轍;如俠少的狂歌,農工的高唱,粗豪之極,卻不是沒有腔調;他是蓄儲著過多的天才的,隨筆揮寫下來,便是晶光瑩瑩的珠玉;在音調的鏗鏘上,他似尤有特長。他的詩篇幾乎沒有一首不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尤其是他的長歌,幾乎個個字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吟之使人口齒爽暢,若不可中止。”
李白將功名、尋仙、俠客、飲者,游走江湖集于一身。李白的樂府歌行體長詩,雍容華貴,筆若懸河,傾瀉不絕,《將進酒》開卷氣吞斗牛,一任想象馳騁,盡遣萬斛珍珠,寫黃河之來也,天地無窮;二句急轉直下,青絲白發,人生短暫,朝暮而已,寫流光之逝也!無限感慨之下,“將進酒,杯莫停”,因為“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李白被貶,作《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寫一種告別,也是出發,“明朝散發弄扁舟”也。
胡應麟《詩藪》稱:“太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篇神物。”李白在此類作品中表現的,是想象瑰麗,是詞語俊俏,是意境蒼茫。如《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這一首七言絕句盡顯語言錘煉之功。峨眉山,天上月,平羌江,清溪,三峽等等,不是嵌入的,而是一體的。其五言絕句亦天人合璧,如:“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李白以謫仙聞名,而梁啟超則以“情圣”論杜甫:“中國文學界寫情圣手,沒有人能比得上他。”
杜甫主要成就在安史之亂后。杜甫對社會動蕩有著極敏銳的感覺。在他四十歲之前,安史之亂還未發生時,便預感到了山雨欲來。如《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詩以濃墨點題,次第展開的,是一幅“爺娘妻子走相送”的長卷別離圖。用的是通俗口語,爺娘妻子口中出。經過情感的浸潤,成為杜甫筆下詩的語言。令人驚奇的是,杜甫怎樣醞釀、錘煉、整理語言,并使之戛戛獨造,如入化境?如果說李白的語言是從天而瀉的,那麼,杜甫的詩句便是從地里長出,與生俱來,生生不息;或者經年累月鑄煉于胸懷,然后噴薄而出。他的想象若風卷云霞雨露,又落在眾生之間;他的情懷能容得四海之內,天下慈悲。“蓄儲著過多的天才”,李杜皆然。沉郁頓挫,其風格也;情感濃郁,其心性也;眾體兼備,其才情也;恢宏博大,其境界也。
杜甫以先知先覺,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乾隆十五年《御選唐宋詩醇》論曰:“攄郁結,寫胸臆,蒼蒼莽莽,一氣流轉。其大段有千里一曲之勢,而筆筆頓挫,一曲中又有無數曲折也。……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板蕩之后,未有能及此者。此甫之所以度越千古而上繼三百篇者乎?”詩自“杜陵有布衣”始,其中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句。杜詩集詩歌藝術之大成,長短詩無不精美。《月夜》寫月,卻是三處月,三處夜,一種境界。鄜州月夜,想象得之;詩人身陷長安而長安月夜未著一字;期待與家人團聚寫“清輝月臂寒”。凡此月色,無不從妻兒落筆,詩情從鄜州天上的月光漫瀉而至:“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杜甫的詩,寫底層民生,卻挺拔浩然,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至今,“安得廣廈千萬間”,不仍是人類的夢想嗎?楊倫《杜詩鏡銓》中贊為“杜集七律第一”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是詞語的典范:通篇對仗,實為律詩之忌。杜甫卻筆無稍滯,佳句連篇。“萬里,地之遠也;悲秋,時之悽慘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極精確。”(羅大經:《鶴林玉露》)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嚴羽稱:“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良可信也!
以李杜為代表的唐代詩人,在詩歌藝術金字塔的頂端,使漢語言成為了獨美世界的語言。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內杜甫雕像資料圖片
韓孟元白
韓孟,韓愈、孟郊也,史稱韓孟詩派;元白,元稹、白居易也,史稱元白詩派。唐代歷史在紛亂不安中,進入了貞元、元和時期,有了中唐詩歌之盛。清人馮班《鈍吟雜錄》謂:“詩至貞元、元和,古今一大變。”葉燮《百家唐詩序》稱,中唐詩非唐詩之“中”,乃“百代之‘中’”。
韓孟二人中孟郊齒長,他一生窮困潦倒,以苦吟著稱。其詩講究煉字造詞,境界奇崛。《送殷秀才南游》:“風葉亂辭木,雪猿清叫山。”《遠愁曲》:“聲翻太白云,淚洗藍田峰。”韓愈稱其“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其《苦寒吟》:“百泉凍皆咽,我吟寒更切。半夜倚喬松,不覺滿衣雪。竹竿有甘苦,我愛抱苦節。鳥聲有悲歡,我愛口流血。潘生若解吟,更早生白發。”孟郊詩寒,也有不盡暖意者,《游子吟》:“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韓孟詩派中,賈島詩瘦,苦吟又苦吟故也。賈島的《絕句》:“海底有明月,圓于天上輪。得之一寸光,可買千里春。”《題詩后》:“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題李凝幽居》:“閑居少鄰并,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云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一瓢詩話》稱:“賈島詩骨清峭。”韓愈有《贈賈島》詩:“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風云得暫閑。天恐文章渾斷絕,更生賈島著人間。”
清人趙翼寫《甌北詩話》說韓愈,“辟山開道,自成一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鄭振鐸謂:“而他的才情的弘灝,又足以肆應不窮,其結果,便樹立了詩壇上的一個奇幟,一個獨創出來的奇幟。”韓愈集奇險、崢嶸的物象于一爐,如《苦寒》:“兇飆攪宇宙,铓刃甚割砭。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頻窺覘。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南山詩》連綿二百多行中,以五十多個“或”字開頭,寫山石巖崖之千奇百態,“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翩若船游,或決若馬驟……”想象如風狂雨驟,詞語若高山瀑布。
李賀有韓愈風格,“險怪如夜壑風生,瞑巖月墮”(謝榛語),有鬼才之稱。其《李憑箜篌引》,一鳴驚人。
在韓孟詩派稱雄之際,能我行我素的,是柳宗元、劉禹錫。柳詩無艱深怪異,因著人生蹉跎,他的詩多內向的追思。《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劉禹錫寫《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又寫《竹枝詞》:“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趙翼認為:“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峻,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如果說韓孟派的詩,像枝葉落盡的冬日;白居易一派的詩,卻如春水盈盈,波光流轉的了。”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中國詩史上,李賀《李憑箜篌引》之后,又一首寫音樂且影響更廣的作品。音樂之聲何能寫,何能說?能說能寫又何必音樂?其知難而寫,而妥切者,而比之急雨,私語,大珠小珠落玉盤,想象奇崛動人心魄者,其聲若鶯語,流泉,銀瓶乍破,鐵騎突出,四弦裂帛,躍動在字里行間者,非天才不能為也!在唐詩人的序列中,李杜之后,韓愈繼之,韓愈之后,白居易為重。“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句,歲月不能磨損其毫末,感慨聲至今猶在。元稹與白居易,相與桴鼓,互為木鐸。元稹《離思五首》之四:“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行宮》:“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與元稹同時的樂府詩人李紳,僅存至為珍貴的《憫農二首》,“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句流傳千古。
有唐一代,懷古詠史,均出現在時代風云交會時。晚唐詩壇杜牧和李商隱,史有“小李杜”之稱。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云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里,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有杜詩之“沉郁”也。
李商隱,字義山,他的文學主張是:“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嘆以通性靈。故陰慘陽舒,其途不一,安樂哀思,厥源數千。”他注重人的七情六欲,主張詩應書寫性靈、情感和欲望,他用詞怪險,造句艱深。敖器之說他“綺密瑰麗”;程夢星說他“詭譎善幻”。無題詩是他的獨創,七律是他的奇葩。如《贈劉司戶蕡》:“江風揚浪動云根,重碇危檣白日昏。已斷燕鴻初起勢,更驚騷客后歸魂。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李商隱《詠史》句乃千秋萬代座右銘:“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破由奢”之明證者,《隋宮》也:“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李商隱的《無題》詩,意境奇特,詞語隠微,《無題四首》之一:“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又《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李商隠詩中的形象,時或冷峭,時或斑斕,時或夢幻。“旨意幽深,婉轉動情,有如一顆藍寶石,閃爍著迷人的光彩,吸引著世世代代的讀者”(《唐詩鑒賞集》)。凡落花,垂柳,詠月,詠蝶,均有佳作。“遠恐芳塵斷,輕憂艷雪融”,芳塵能斷雪可艷,李商隱之詞語也;“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柳絮飄飏花有心,李商隱之風情也。
吳喬《圍爐詩話》說:“于李、杜、韓后,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他的貢獻既不在題材,也不在體裁,而是他的語言。李、杜、韓之后,白居易以平易淺近的語言寫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李忱:《吊白居易》);李商隱則鑿險縋幽,情思婉轉,意境要眇,獨構“沉博艷麗”“寄托深而措詞婉”(葉燮:《原詩》)的風格。
有李商隱承前啟后,唐詩堂廡深廣。唐詩幸哉!中國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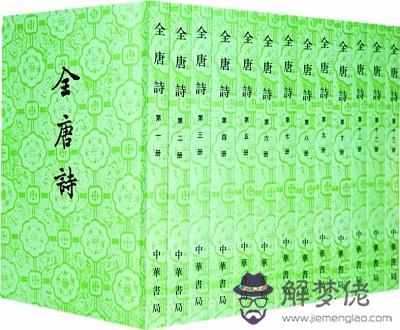
尾聲:驀然回首
驀然回首,是一種意象,也是尋覓和訝異,詩和夢想、情感瞬間萌發的象征。人心里最柔弱敏感的便是情感,而最能觸碰情感的便是詩。唐詩留下了多少獨特的詞語,詩性與神韻,情感倏忽來去的瞬間,“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也。唐詩焉能不讀?焉可不讀?王夫之《俟解》謂:“圣人以詩歌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賢。”然詩由詞語組成,詞語由字組成,詩的語言絕對是不一般的語言。以詩歌蕩滌其心者,必得識字明詞,是有識字聞道說,是有語言文明說。
梁啟超在《國文語原解》中說:“國民之所以為國民以獨立于世界者,實受自歷史上之感化,與夫其先代偉人哲士之鼓鑄也。而我文字起于數千年前,一國歷史及無數偉人哲士之精神所攸托也。”梁啟超告訴我們,我國文字行之數千年,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亦幾千年。文字獨立而民族獨立,文字相續而文明相續。文字之功全賴先代偉人哲士之“鼓鑄”也;鼓鑄者,鼓風揚火陶冶錘煉文字、詞語之謂也,然后有詩。人類學家李濟認為,漢語“在動蕩變遷中留存至今,它已保護了中華文明四千多年。它是穩固的,方正的,正如它代表的精神一樣美麗”。漢語言的重要性于此可見。
想起了屠格涅夫在《莫斯科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演說》:“是普希金最后加工了我們的語言……是他用典型形象和不朽音韻,對俄羅斯生活的一切潮流作出反應。最后,是他第一個用強有力的手臂,把詩歌的旗幟深深插進俄羅斯的土地。”屠格涅夫在《關于〈父與子〉》的結末處,對年輕的俄羅斯文學家們的“最后的請求”是:“請愛護我們的語言,愛護我們美妙的俄羅斯語言,這一寶藏,這一財富,是以光輝的普希金為首的先行者傳給我們的!”
朋友們,請愛護我們無比美妙的中國語言,請銘記那些比普希金更早的、使中華民族成為詩性民族的、“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的偉人哲士。請珍愛來自遠古的情感和詞語,還有驀然回首的感動。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20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132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