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梵(詩人、小說家)
五十一年前的今天,4月20日,這個被德語詩人保羅·策蘭自殺撕開的日子,仿佛是一個永遠的提醒:現代文明,是一種多麼奇怪的文明,里面包含了太多讓人,尤其敏感詩人,無法承受的悖論。因為意識到策蘭生命的結束,也預示著新的挑戰開始,為了繼續挖掘他深藏和帶走的秘密,漢語出版界已趕在今年祭日前,出版了數種有益的漢譯選本,我手頭就有黃燦然譯的雅眾版《死亡賦格:保羅·策蘭詩精選》,王家新譯的純粹版《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歷史上有眾多的詩人之死,但策蘭之死的意義,大為不同,他的死已關乎構建現代文明的基石,即美的技術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美是否真的可以超越倫理?

保羅·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二戰以來影響最大的德語詩人;1952年,其成名作《死亡賦格》震撼德國;1960年獲德國最高文學獎——畢希納獎。其作品備受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阿多諾、哈貝馬斯等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家推崇。著有《罌粟與記憶罌粟與記憶》《語言柵欄》《無人的玫瑰》《棉線太陽》等多部詩集。
猶太身份與母語的悖論體驗
德語詩人策蘭的故事,起初并沒有超出普通猶太人命運的范疇,他們的存在感體現在恪守的文化中,并不像中國人有國家可以忠誠,哪里是他們可以信賴的故鄉,始終是困擾他們的問題。比如,策蘭的故鄉澤諾維茨,就經歷了隸屬奧斯曼帝國、羅馬尼亞、蘇聯、德國等的數度易主,每一次的變更都意味著猶太區要經受新的沖擊,畢竟后來的新主并無奧斯曼帝國的氣度,可以開明寬容地對待猶太文化。猶太城數度易主的慘痛,我們可以從另一位猶太作家巴別爾的小說,如《泅渡茲勃魯契河》中,窺見一斑。策蘭故事真正的不尋常,我認為,起于從小母親堅持幫他維護的“母語”:標準德語。這是他一生最擅長的語言,令他思維的語言,從小就與猶太的文化、語言、方言有所隔膜,這種猶太身份與母語的悖論體驗,隨著他日后踏上詩壇愈發明顯。他曾在《旅伴》中這樣寫母親:
這個詞受你母親的監護。
你母親監護的詞共用你的鋪位,一塊又一塊石頭。
你母親監護的詞俯身拾起光的碎屑。
——黃燦然譯
詩中母親的形象更像嚴厲的教師和父親。這里有一個他少年時的隱情:他當時受到兩種文化和語言的爭奪,一方是母親的德語和德國文化,另一方是父親的希伯來語和猶太教,他十三歲時,內心的天平傾向了母親一方,他不再對希伯來語用功。這意味他的猶太特性必須接受德語的喬裝打扮,也意味父親要通過母親才能對他說話。這可以解釋,為何一方面父親被他后來的詩歌“遺忘”了,他鮮有涉及父親的詩作,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在猶太人的家庭里,卡夫卡那種怨天尤人的《致父親的信》,必須反復書寫”(費爾斯坦納《保羅·策蘭傳》,李尼譯),此外讀者還能在他沉迷談論母親的詩作中,尋到父親的蛛絲馬跡。比如黃燦然認為,《一切都不同于你想象的》的中心人物,是曼德爾施塔姆和母親,“他也把它拿去,你再次擁有/那屬于你的,那曾是他的,//磨坊”(黃燦然譯)。我大膽猜測,父親已與曼德爾施塔姆合二為一,成為他失而復得的猶太精神靠山。
這種起于少年而貫穿一生的困擾,還可見于《從黑暗到黑暗》:“……那是渡輪嗎?在過海時醒來?/會是誰的光在我腳跟照耀/迎接一個擺渡人出現?”黃燦然認為,“擺渡人”這個隱喻,可以視為策蘭把自己作為猶太人的他者身份,運送到當代德語領域里。黃還提到斯坦納的論斷:策蘭自己的全部詩歌都是被譯“入”德語的。我想說,這樣的“譯入”已發生在策蘭早年,那時他已經需要讓他的猶太生活,進入他思維用的德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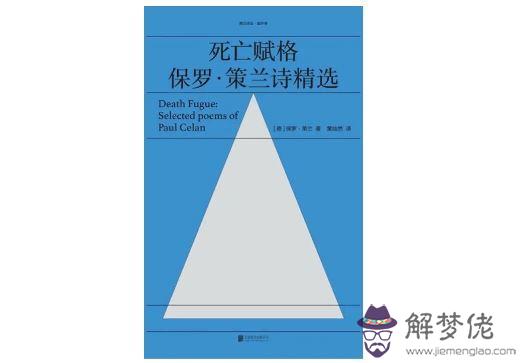
《死亡賦格:保羅·策蘭詩精選》,[德]保羅·策蘭著,黃燦然譯,雅眾文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1月。
他母親一直嚴防死堵猶太方言進入他的標準德語,這番努力造成的終生困擾,對用普通話思維的部分中國南方人并不陌生。普通話令他們“忘掉”了故鄉的諸多事物,當他們竭力用普通話打撈“失蹤”的一切,他們同樣面臨黃燦然說的“沉默屏障”。只不過,他們是要把經歷的個人生活,從普通話的沉默中運出,讓它翻越“沉默屏障”,開口說話。策蘭早年就經歷了這一切,只是成年后的慘痛生活需要他從沉默中運出的,是與大屠殺有關的一切,這任務不止艱巨,精神上也格外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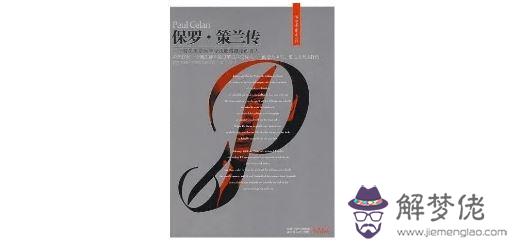
《保羅·策蘭傳》,[美]約翰·費爾斯坦納著,李尼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揭示現代性的悖論
當然,事情遠不止這麼簡單。詩人竭力運出難以言傳的苦難時,他高人一籌的技藝,甚至“言不及義”,往往會被人誤解。單單就說漢語界吧,疊加在《死亡賦格》上的誤解,至今沒有消散。這首1947年發表,漸漸轟動和震撼起來的成名作,其實也是他后期詩作的源頭,兩者形式迥異,藝術思想卻一脈相承。哪怕策蘭后來甚至拒絕公開朗誦它,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把它與策蘭的后期詩作,比如《密接和應》等割裂看待,甚至用后期詩作的成就,“蔑視”《死亡賦格》的成就和思想源頭。
我認為,黃燦然對《死亡賦格》的注釋中有一段詮釋策蘭的話,可謂一語中的:“策蘭堅持認為《死亡賦格》并不是一套生動的意象、巧妙的形式設計或富有創造性的文字游戲,不能以‘為藝術而藝術’的方式來讀,因為它與現實是不可分割的。它是要被感受的,而不是要被贊嘆的。”是啊,《死亡賦格》中描繪的數段音樂意象,不只是集中營的現實之一,也含著對納粹把音樂之美技術化的控訴:
他大喊挖深些你們這伙你們其他的唱歌演奏
他抓起皮帶上的手槍揮舞著他眼睛是藍的
鏟深些你們這伙你們其他的繼續演奏舞曲
……
他大喊把死亡演奏得甜蜜些死亡是一個來自德國的大師
他大喊把提琴拉得黑暗些你們就可以化作輕煙飄入空中
你們就會有一個云中墳墓那里躺著不擁擠
——黃燦然譯
詩歌涉及了納粹美學的實質,納粹試圖把美像科學那樣中性化,剝離美中富含的人性和倫理,像應用毒氣等殺人技術那樣,把美應用到殺人場景。我認為策蘭是用音樂意象,測度了納粹的超然美學,這樣的美學竭力追求整齊干凈。一旦把整齊干凈用于血統,猶太人就成了納粹眼中的雜質,非整齊的異類,用于書籍,納粹就會焚書……如此超然的美學從何而來?實際上,很多人的思考到此就會停下,這是割裂策蘭前期和后期詩歌的癥結所在。只要回到啟蒙運動的理性至上,就能發現這種美學的源頭。
按照理性主義的設計,人類會有完美的未來。一旦用理性去設計未來,無數人對未來設想的差異,就會消失。理性的本性是趨同,就是被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夸為文明法寶的共識。共識的審美本性就是消除差異,獲得整齊干凈之美。這就是現代文明隱藏的理性之病,文明得于理性也病于理性。策蘭以自己的苦難經歷,和使用標準德語的艱難寫作,早已窺見了現代性的悖論。這樣就可以理解,他為何不滿足阿多諾的說法:“在奧斯維新之后,寫詩是野蠻的。”
阿多諾意識到奧斯維辛是一個標志,標志著現代理性已把美徹底技術化,美已可以殺人。當一些中國詩人竭力與“詩言志”的傳統脫開干系,他們不知不覺,就進入了阿多諾說的野蠻之境。策蘭可以說,是用《死亡賦格》來回應阿多諾,詩展示了屠殺之地,異常理性的黨衛軍,如何讓音樂之美與人性、倫理脫鉤。單世聯的文章提到法國人范妮婭的回憶,證實了這樣的脫鉤遍布集中營。范妮婭曾擔任集中營女子樂隊的指揮,一天為黨衛軍舉辦露天音樂會,其間有一個婦女沖向電網自殺,她的朋友沖過去想救她,結果兩人一起掛在電網上抽搐。黨衛軍則超然度外,“相互拍著背,笑著”聽音樂,演奏結束,“黨衛軍笑著,站起身,高興地評論著”音樂,對電網上的慘劇熟視無睹。很多人沒有看出《死亡賦格》,正是對這種脫鉤的諷喻,控訴。甚至有人還抱怨,詩中的音樂等意象,美化了大屠殺。
策蘭用詩寫道:“他黃昏時寫信回德國你的金發瑪格麗特/你的灰發書拉密”“死亡是一個來自德國的大師他眼睛是藍的”(黃燦然譯),瑪格麗特是歌德《浮士德》中被拋棄的女子,代表基督教,書拉密是《圣經·雅歌》中的猶太女子,代表猶太教,“多愁善感”的黨衛軍給她們寫信,他眼里有冷酷到可以殺人的藍色,代表理性,誰都能感到他們之間的悖論、嫌隙和不協調。詩中黨衛軍用理性安排的美,殺人時的音樂之美,寫信給瑪格麗特和書拉密的多愁善感之美,兩者在黨衛軍身上合二為一,正揭示了現代性的悖論。

保羅·策蘭在巴黎的公寓中,1958年。
清洗“污跡斑斑”的德語
策蘭已經意識到,從中世紀宗教解放出來的理性至上,同樣暗藏著野蠻之力,《死亡賦格》對這種理性的諷喻,顯而易見,可以說,與阿多諾的洞見是一致的,只是表述不同,策蘭的隱語是,可以被書寫的詩,再也不能清除倫理。只有靠著倫理的點撥,我們才容易看清策蘭后期詩歌的壯舉。正是覺察到了理性在標準德語中的妄自尊大,甚至掩飾殺戮的虛偽,策蘭才會懷疑標準德語的正常之美,不再滿足像《死亡賦格》那樣,用德語的正常之美進行諷喻,他要直接擺脫標準德語的標準,通過創造新的語境甚至語法,來清洗“污跡斑斑”的德語,用他渴望獲得的純凈語言,傳遞他身上的猶太特性。比如,按照黃燦然的注釋,《密接和應》中草的意象,是提示與猶太人有關的舊約,《法蘭克福,九月》中的“‘最后一/次心理/學。’//偽/寒鴉/吃早餐//喉塞音/歌唱”(黃燦然譯),會讓人想到卡夫卡,“最后一次心理學”是卡夫卡用過的句子,“寒鴉”的捷克發音是“卡夫卡”,他用“偽寒鴉”自詡偽卡夫卡。他后期詩中更大的力量,是渴望用自己創造的純凈語言,對文明災難全神貫注。比如,他用《一片葉子》反駁布萊希特的《致后代》。布萊希特用詩說:“當/一次關于樹的談話也幾乎是一種犯罪/因為它暗示對許多恐怖保持沉默?”(黃燦然譯),策蘭用詩回應道:“當一次談話/幾乎就是犯罪/因為它包含/如此多說過的?”(黃燦然譯)。

保羅·策蘭和妻子吉賽爾·策蘭-萊特朗奇。
德國人通常給中國人留下反省歷史的良好印象,策蘭后期詩歌要面對的倫理困擾,正好可以讓我們感受到當時不少德國人,在遺忘和反省之間的猶疑不定。所以,策蘭想擺脫德語,又不得不依賴母親給他定制的這一母語,是他后期寫作的悖論之旅,艱難和難以完美,可想而知。單從雅眾版《死亡賦格:保羅·策蘭詩精選》就可看出,試圖忘掉語言標準的詩作,就占了詩選的大半。就算黃燦然根據漢語需要,做了容易讓讀者理解的翻譯“補救”,策蘭的后期詩作仍受到“難懂”的困擾,《密接和應》首當其沖,可謂難懂之首。我對比過黃燦然、王家新、孟明的譯作,真是各有千秋。黃燦然著眼讀者能明白甚至追上策蘭的思路,竭力化開語言的結節,王家新著眼詩意的創造,會保留語言的結節……黃燦然作為詩人,一向不蔑視生活,他的譯作也追隨了這樣的詩學,賦予了這本策蘭詩選,難懂之中的“可讀性”。
草,被拆散來寫。石頭,白,
帶著草葉陰影:
別再讀了——看!
別再看了——走!
……
沒有看,沒有,
談論
詞語。沒有一個
醒著,
睡眠
已經來籠罩他們。
——《密接和應》黃燦然譯
策蘭想穿越德語的標準之墻,就是為了求得美與倫理結合的正道,他一人獨行,遠離一切標準時,譯者利用翻譯理解的時機,竭力讓讀者也追隨他的理解,這樣產生的可讀性,于策蘭的詩作同樣是貢獻。喚來不同的理解,本就是經典的意義所在,就像莎士比亞一旦置身德語,就會高于德語中的但丁。
策蘭進入漢語,起于王家新和芮虎的譯介,接著北島、黃燦然、孟明陸續投身其中,黃燦然以中國人容易接受的清晰漢語,同樣讓我們感受到了策蘭前后期詩歌的悖論之美。這美的鎮定和端莊背后,是籠罩在策蘭身上的神秘困境,本質上也是現代性的困境,如他在《黑》中所寫:“命名總有結束的時候,/我把命運投到你身上。”(黃燦然譯),“你”指的是“黑”。真是一語成讖啊!他徘徊在代表西方文明的塞納河邊,始終沒有找到解決之道,他以縱身一躍的詩人之死,把自己的命運投到了塞納河的黑暗中,正如他在《當白色襲擊我們》(黃燦然譯)所說:
當皮開肉綻的膝蓋
向那奉獻儀式的鐘聲做出這個暗示:
飛呀!——
作者 | 黃梵
編輯 | 青青子 羅東
校對 | 趙琳
來源:新京報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09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