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張瑩瑩
1
桌子不大,窄長,圍著大紅或墨綠絲絨桌圍子,上面鋪著同色的一塊布,往下耷拉半截,垂著黃穗。桌子后頭,椅子比一般高些,說書人坐上去,不能實打實,屁股跐著一點邊,胯跟桌子平齊,時間長了比站著還費力。就得這麼坐著,取的是高臺教化的意思。
隨時都能站起來,往往是比擬人物,上身有些個動作。要是人物動作太大,這人就得右跨一步,離開桌案,顯露出全部身形。正經是一身大褂,中式對襟上衣也行,下著黑色水褲,褲腳扎著,滿露出來圓口黑布鞋里頭套著白襪。偶爾也有人穿著西裝皮鞋,遇見這樣的,觀眾就要猜這演員是不是今天得趕場,除了說書又接了別的活。
算不上書迷,我的評書經驗可能跟大部分年輕人類似:小時候在電視上、廣播里,避不開地聽過幾耳朵《白眉大俠》、《楊家將》,2005年后,聽過郭德綱的相聲和單口,近幾年,隨著音頻APP的興起,又隨便聽了幾回評書。2017年冬天,我想聽聽現場評書,通過大眾點評,找到了前門老舍茶館。
前門是游客圣地,茶館賣的是“來京必看”的老北京風情,曲藝,包括相聲、評書、大鼓等等,是這風情的內容。那天人不多。我剛在書館坐定,戴黑色瓜皮帽、穿著寶藍大褂、肩頭耷一條白毛巾的伙計便端上蓋碗,黃底上描著京劇臉譜,揭開,是老北京人愛喝的茉莉花茶。他在座間穿梭,用一把紫銅茶壺開蓋續水。
臺上,穿著黑大褂的年輕男孩在說《水滸》,矮腳虎王英就要被人殺于馬下,但場里氣氛并不聚攏,十幾個人,多是來京游客,帶著大包小包,有人小聲聊天,有人低頭閉眼仿佛睡著,有人哄著孩子,那孩子漸漸從哼唧變成了哭鬧。大褂男孩抬眼看過,又繼續說王英。一個小時后,他拔高聲音,摔了醒木,下得臺去。
穿一領磚紅大褂的男人掀開繡著鳳凰的簾幕,手握包著扇子和醒木的白手帕卷,走上前來,微微鞠了一躬,椅子上坐下。年紀不大,留著略長的頭發,額前那一片修剪過,正眉間有個豁口,恰露出眉心一顆痣來。“給您換一場”,他仰著頭,聲音亮堂。人群好似醒了一層,都望著他。
他說的是《三遂平妖傳》,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之前的作品,最為大眾所知的信息,是它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改編成動畫片《天書奇譚》。動畫片講的是一個孩子和三只狐貍,小說卻是成年人的故事。宋仁宗年間,奸臣當道,妖人造反,丞相包拯平滅叛亂,又是清朗人間。這一回說到蛋蛋和尚(動畫片中的蛋生)重現開封府,三戲包相爺。說書人賣著好,“您各位是來著了,這一回正是本書的熱鬧回目。”
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里,他將三次戲耍細細鋪排,節奏或緩或急,時不時有些包袱,我精神一直在跟他走,雖然也會時不常看看手機。他語調清脆,帶著一點不吝勁兒,時而站起來,捏著白手帕一角模仿被戲弄的綢緞莊老板娘,腔調是細的,臉和身段都是媚的。又學站在旗桿上的蛋蛋和尚,對包拯大加譏諷。座中嬰兒又哭鬧起來。說書人沒翻眼皮,敘述還在蛋蛋和尚的話里,突然道了一句,“怎麼哭起來還有奶音兒呢?”
人群靜了一秒——反應了一下,隨之大笑,拍手。我發現,現場評書比網上那些20多分鐘一段的靜場書好玩多了。散場后,我四處打聽第二位演員叫什麼名字,有人問到正在臺子旁一個小房間里收拾的人,他臉上帶點年輕人里常見的“躁”,左耳上掛著三只黑耳釘,“就是我啊!”一個有點“葛”的北京孩子,一點不像想象中的“說書先生”。
他叫鄭思杰。

鄭思杰在老舍茶館。由作者拍攝。
2
有好些年,北京沒什麼曲藝演出的地方,鄭思杰記得,2005年之前,他只能在春節廟會上演,說相聲,唱快板。天寒地凍,老百姓擠擠挨挨,臺上的鄭思杰大褂里套著羽絨服,膨起的絨把大褂撐得鼓鼓囊囊。一下臺就找管事的要暖水瓶,可露天里暖水瓶放久了,水也冰涼。說一場只有三五十塊,為的是鍛煉,別怕見生人。
鄭思杰是北京人,1990年出生,8歲學快板,拜的是快板書名家梁厚民先生。梁先生會得多,教他快板,也教相聲、評書。鄭思杰不拘門類,愛的是曲藝這種生于民間的藝術形式。
說到評書,鄭思杰先是聽,2003年北京非典那年,他跟家里磨出來1500塊,從王府井書店買了袁闊成先生一套《三國演義》VCD,翻來覆去地聽,聽到好詞兒就記,不一定知道什麼意思,就覺著好。2008年高中畢業的暑假,師父把他推薦到上海南京路新開的相聲會館里,他每周五六唱快板、說相聲,二三四就說書,才十八歲,愣說了倆月《封神演義》,沒那麼大膽像“袁爺”袁闊成那樣從女媧宮降香開,他先說的哪吒鬧海,熱鬧,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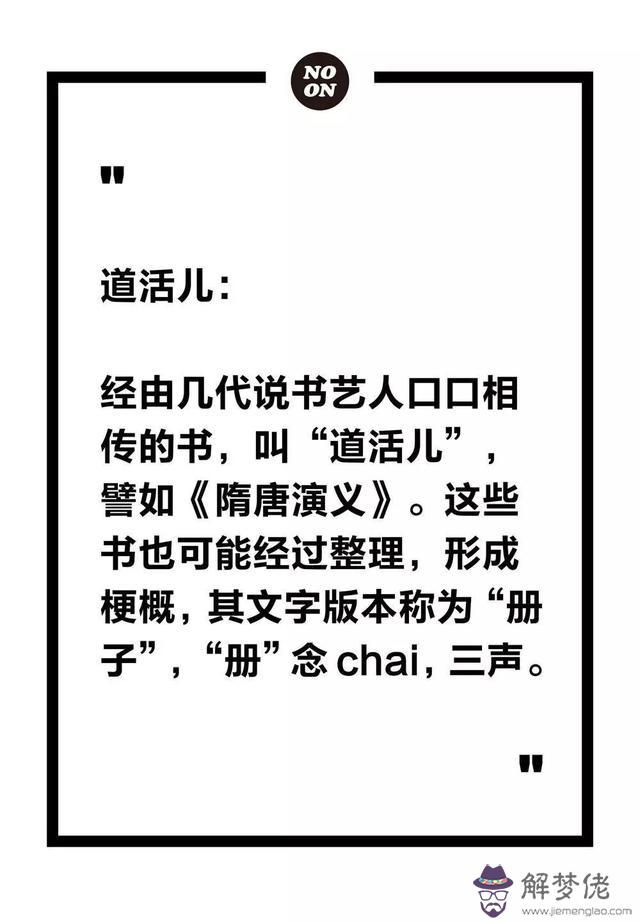
評書行當常講一句話:說書說的是人情事理。以往學說書,學徒先在茶館里倒上三年茶,為的是聽書,聽差不多了,到師父家里去,師父給說一段,學徒重復一遍,天天磨,加上對世態人情的體悟,到學成得二十多歲快三十。
鄭思杰想往深了學評書,但評書市場一直不景氣。很長一段時間他還是靠相聲和快板換錢。他去過好多亂七八糟的地方演出,夜總會,洗浴中心,燈光迷離的酒吧,穿著網兜跳鋼管舞的兔女郎下去,穿著大褂的他上來。即使是正經劇場演出,相聲越來越走下三路,他有點煩。
2015年底,鄭思杰和老舍茶館談了合作,將二樓一個一百來平的空間做成書館,每周六下午演出,茶館和演員分成。說書成了他主要的行當。他不愿意提“說書先生”、“高臺教化”這些詞兒,好像一說書就得拉開那個架勢。那是早年間老百姓不識字,靠說書先生拉典長見識,現在,他本科畢業,聽書的碩士博士都有,談不到他“教化”。
最撓頭的問題是,說什麼?
傳統書老先生都說過了,說得好,“八個鄭思杰擱一塊也比不過一個袁闊成去”,還不要錢,隨便聽。如果他去說傳統書,誰愿意花錢聽他的呢?觀眾也變了,以往說書要“留扣”,現在一上網,觀眾馬上知道下一回的情節,沒有懸念。“不夠吃的”,鄭思杰說,“就得找新的。”
評書行當其實一直在“找新的”。1949年7月,連闊如出席第一屆全國文代會,創編新書《夜渡大渡河》。解放后,許多傳統書不讓說了。袁闊成帶頭說新書,《野火春風斗古城》、《林海雪原》等新評書廣泛傳播。“文革”期間,金文聲在大學校園里翻到外國小說,改編成評書《基督山恩仇錄》、《三劍客》和《茶花女》,是將外國書改成評書的較早嘗試。網絡傳播時代,年輕一輩的評書演員也在求新,王玥波曾受土豆網邀請改編漫畫《火影忍者》,葉蓬說過《霍比特人》。共同特點,原著都是“大IP”,說是噱頭也好,得讓沒有聽書習慣的年輕觀眾知道;同時情節曲折,戲劇性強,適合改編成評書。
鄭思杰琢磨了不少“新書”,《三遂平妖傳》是其一。這書是他從小說改編的,情節安排、節奏處理,全靠自己掂對,還得用今天的思考賦予人物從無意識到“壞”的邏輯。說起來也都是用現在的話,沒有“分列兩旁、大排筵宴”,他說的都是“來來來,吃吃吃!揀貴的吃!”但因為說的是包拯、寇準,不明就里的觀眾還把它當傳統書對待。
他又琢磨起了外國書。《堂吉訶德》挺好,就是中國版的《書迷打砂鍋》,一個入迷的人鬧出一連串笑話。真著手編排,他覺出外國書麻煩了,時空久遠,不容易找到十六七世紀的資料填充評書需要講述的細枝末節處,同時,他的觀眾,21世紀的中國年輕人,也很難理解為什麼一個人要為了個根本沒見過的公主奮不顧身,邏輯就不匹配。
“拿話構建一個邏輯太難了。”鄭思杰說。
去老舍茶館聽過幾回書后,我約了鄭思杰,本意只是想了解一個傳統行業從業者在今天的生活狀態。老舍茶館書館的上座率一般,能坐一百人的場子,多的時候三十來人,少的時候七八人。現場買票58,團購38,這錢去掉場租還得兩三個演員分,怎麼算也不是個好買賣。鄭思杰耐心地對我進行了一番評書知識普及,又提到想說“新書”,提到《堂吉訶德》——我驚訝極了。從沒想過這兩樣東西能擰到一塊,能行嗎?
暫時他沒做出成功的例子,“小說和影視不需要跟觀眾直接交流,都有介質,可以虛構;但我們這個沒有介質,咱們都是現實中的人,憑什麼你講一個不現實的事兒?外國書不好說就在這里。就說名字,一大串,聽的和說的都記不住,可是要改成中文,老王小張,外國書沒了,中國元素太多,又有點違和。”
放棄《堂吉訶德》,鄭思杰又改編了東野圭吾的小說《白夜行》。這部書比《堂吉訶德》時間空間都近,便于中國觀眾理解,但平行結構給鄭思杰出了難題:小說可以讓兩位主角在顯現的文字中從無交集,一星期演出一回的評書卻很難建立平行時空。評書是口頭藝術,依靠時間的連續,“一張嘴難說兩家話”。《白夜行》處處打破了傳統書的套路。鄭思杰設想,這一周說桐原亮司,下一周說唐澤雪穗,但隔開太久,又是偵探小說,線索得一直留著、給觀眾提醒,勢必每次說都要大段倒書,也不是個辦法。或者錄靜場放網上,聽書人能一股腦聽完。左思右想,評書《白夜行》說到小說第二章開頭,也是這本書真正開始走兩條線的時候,鄭思杰停了下來。
他不愿意把話說死了,說外國書難是難,但他還在琢磨,還想嘗試。
再找書,喜馬拉雅給他推薦了小說《古董局中局》。鄭思杰看過這小說,覺得挺合適,主要人物明確,“書膽”有了;過場人物層出不窮,“書筋”也有了;主角為了尋寶從北京往外走,沿途經過河南、山西等地,評書說到這兒,盡可以撕出去講風土人情,還能用上“倒口”活,表演空間大。鄭思杰下了心,細編排了一遍,開場介紹主角的小店,門外的對聯,屋里沿墻一格一格的擺設,都是原文沒有的,他憑著自己的想象與見識填充得細節豐滿,一一道來,在評書技法中,這叫“擺砌末”。頭回書上臺說之前,詞兒都給打出來默過,寫了得有幾千字。他滿心想把這部書打造成自己的作品。
沒有版權。他又卡住了。雖然有人說評書是“什麼書都能說”,但口頭形式要求它的底本最好人物連貫,情節緊湊,戲劇性強。近年來中國的通俗文學作品匱乏,適合改編成評書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合適的,也早被影視行業的大資本盯上。鄭思杰在微博上給《古董局中局》作者馬伯庸發過私信,人家沒理他。這事又擱下了。
3
可作為鄭思杰“標簽”的“新書”是《斗破蒼穹》,從2015年10月說到現在。
小說《斗破蒼穹》于2009年到2011年在起點中文網上連載,作者天蠶土豆,1989年出生。這部小說有526萬字,目前在起點上有超過一億六千萬次點擊。它虛構了一個叫做“斗氣大陸”的地方,沒有法律,只認強力。主角名叫蕭炎,借助民間小說中常見的“施惠者”角色,也就是一位得道高人的幫助,加之自己的努力,蕭炎所向披靡。所有女性都傾慕他,男性要麼臣服,要麼被他殺死。
經過上文說到的幾次嘗試,改編《斗破蒼穹》對鄭思杰而言像是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它是“新書”,但是中國語境之內的。經過喜馬拉雅牽線,版權也解決了,這部評書做成付費,和喜馬拉雅分成。
鄭思杰最初設想把小說揉碎了往傳統評書中的短打書和神怪書上靠。中規中矩地,上臺先來一首定場詩,人物出來先開臉,念的也都是傳統書里那套贊賦,情節往緊湊了說,好顯得熱鬧。
逐漸覺得怪。有一回,他說到書中一位上了年紀的人物,用了短打書里常用的套話,“那可是老一發的人物字號。”他并未想要把它處理成包袱,座下卻有人笑。隨即他明白,這是雜糅帶來的違和。
那會兒,他說《斗破蒼穹》已經快一年。在傳統評書大量套路性的言辭之外,鄭思杰需要尋找自己新的語言。在臺上他腦子里一邊過情節一邊想怎麼說。老詞兒不能說,新詞兒又沒有,一個最擅長說話的人突然嘴不利索。他又去聽袁闊成的《野火春風斗古城》,看他敬重的前輩是如何在自己的時代說新書。幾個月后,他漸漸覺得順嘴了。
傳統書除了語言的套路,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套路:臉譜化。好人就是“鼻直口正大耳朝懷”, 壞人就是“塌鼻梁癟山根”。大部分主角人物是“英雄好漢”。
鄭思杰也曾想把蕭炎塑造成英雄,最初的回目里,他強調蕭炎性情沉靜,不茍言笑,修煉認真,有所擔當——像個年輕的展昭。
但他逐漸發現蕭炎不是英雄,他耍雞賊,肆意殺人,伺機摸女人的大腿,毫不掩飾利己的目的。“蕭炎”像是個人主義的極致形象,跟以往評書中的主角完全不同。
“撂地長出來”的評書,宣揚的總是最大范圍的普通人所能接受的道德和價值觀,史書《三國志》到話本《三國演義》中劉備形象的改變便能體現這一點。鄭思杰為蕭炎找到了不同于傳統評書的新形象,“一面正經、一面不著四六”的“半成功人士”,“有點像王思聰”,是今日的偶像。
2018年春節,我聽完了喜馬拉雅上的評書《斗破蒼穹》,一回現場書截三段算一回音頻,一段一塊錢,優惠價九毛,已經更新了300多段。每段的播放量在幾百到幾千之間。壓縮了兩年多時光去聽,評書《斗破蒼穹》前后變化是顯著的。鄭思杰找到了自己的語言,他大量使用北京方言、歇后語、俏皮話和擬聲詞,創造出一個活靈活現的、充滿當下娛樂感的世界。
他不再費心營造那熱鬧的打斗場面了,就他的閱讀經驗,看到大段的打斗場景也會跳過去,觀眾的心態也差不多,評書行進到打斗環節,“歘歘歘歘幾道綠光閃過——反正你也知道怎麼回事”。他不再試圖如小說那般構建一個虛擬世界,“現在人更實質,幻想的事兒大家都沒那麼感興趣了”。越往后,他越離開這部創作于2009年到2011年的網絡小說——僅僅過了幾年,世界好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天蠶土豆的小說讀者還會為因將自己代入而在閱讀中產生快感,幾年后,鄭思杰已經帶著自己的觀眾超越了那種代入,改成一種自上而下觀望的、有點冷漠的了然。沒有人再細琢磨“講理”了,為什麼蕭炎身處險境、永遠不死呢?“因為他有主角光環啊!” 這一句解釋就夠了。
“得跟著社會大節奏去調整。”鄭思杰說。
他覺得社會太浮躁,整個都有點毛病,他就喜歡在家里一個人呆著,看書,畫國畫,寫毛筆字,養鳴蟲,盤核桃。但說書總是需要觀眾的,現場觀眾給說書人直接的刺激,讓他們不斷去調整、創作,以求觸摸到不斷變化的大眾心理。如今,每周五晚上,鄭思杰在護國寺賓館,繼續說這部《斗破蒼穹》。
4
郭鶴鳴是河北石家莊人,1986年出生。11歲,小學五年級升六年級的暑假,他進了當地少年宮開的班,學山東快書。班里20多個孩子,其中18個照過一張合影,在老師家前的胡同里,孩子們大大小小排兩排,郭鶴鳴站在后頭,穿著白襯衫,面容清秀。二十多年過去,現在還在曲藝行當的,也就剩他一個。
學了快板、相聲,到高中,郭鶴鳴又跟隨劉建云先生學習曲藝伴奏,劉是少白派京韻大鼓白奉霖先生的徒弟。曲藝行當約定俗成,按文雅排行,京韻、單弦、梅花算前三,山東快書和相聲都得往后,郭鶴鳴想深造,往上檔次的學。劉老師還給他念過評書,語言身段,他習了些技巧。
2004年,郭鶴鳴高中會考結束,按照師爺的安排入伍。這段經歷給他帶來了一些情緒,譬如憤怒,也帶來了一些收獲,譬如對人情事理的揣摩。在湖北,他“干了這輩子所有的活”,又因水土不服,發燒頭疼拉肚子,得了痔瘡。領導照顧他,讓他去哨所坐崗。日子枯燥,他想起了評書,托人買了袁闊成《水泊梁山》100回盒帶,晚上執勤時聽。
哨所在山里,屋里一開燈,一會兒工夫小蟲子就在天花板上密密麻麻一層。郭鶴鳴把屋里燈關了,合上門,桌子搬到外頭燈桿下,聽一句書,寫一句詞兒。山里真安靜啊,大灰蛾子循著光成群結隊往過飛,時不時撲騰掉他本子上。他還見過一條蛇往屋里爬,拎起一把鐵皮簸箕鏟開蛇,接著寫。這三個月是他評書砸下的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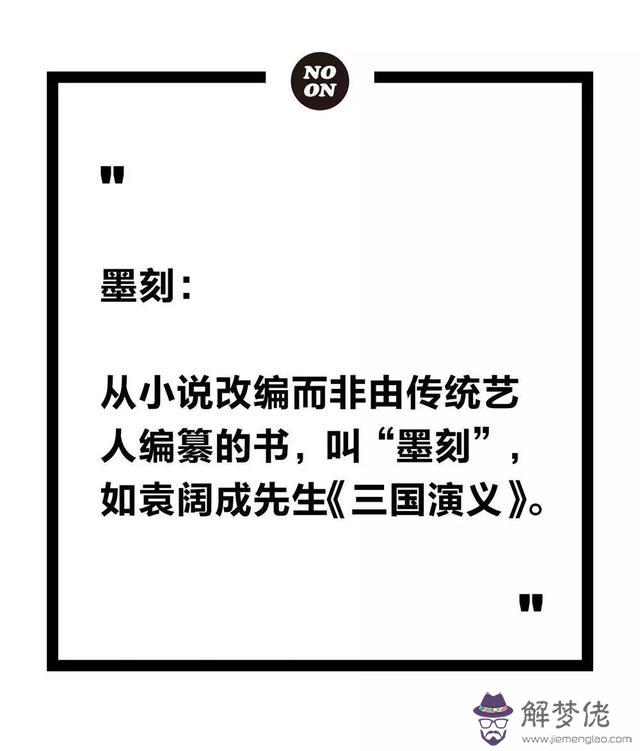
2006春天,郭鶴鳴退伍,通過藝考上了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又進了德云社。因為前一年郭德綱的爆紅,德云社開始擴張,對外招生,郭鶴鳴是第一批學員,每到周末就買12塊錢一張的綠皮火車票從天津到北京上課、演出。那會兒,為給金文聲先生留資料,德云社開了書館,快板、相聲演完,郭鶴鳴就往書館跑,那會兒不經常見到現場評書,他覺得有意思。
后來,金先生病了,書館閑著,郭鶴鳴上臺“愣說”,有時連說仨鐘頭。書館旱澇不保,有過開場時一人沒有,只好對著服務員說;時而只有一兩位,時而60座全滿——全是沒買著對面相聲票被賣票大姐忽悠到書館的游客,臉上掛著三分猶豫七分不耐煩。這樣的觀眾令說書人心里沒底,郭鶴鳴在臺上,有回一天說了夠一個月的書,光怕給少了。他提著一股氣,想把書說好。那會兒他瘦,腰間扎一條綁帶卡在骨頭上,兜住丹田,說完書摘下綁帶,兩條腿才熱乎起來。
德云書館停了一陣,2010年重開。這一回,郭鶴鳴改編清末無垢道人的《八仙得道傳》,變成一部35回的評書。這部書有一些撒湯漏水的地方,郭鶴鳴說,但它對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八仙傳沒有道本,對說書人來說就算“新書”,郭鶴鳴改編,要按評書的節奏琢磨,要查事件背景,往里頭添枝加葉。一番操練下來,他覺得自己會說書了。
尋思下一部書時,郭鶴鳴想到了《哈利·波特》。還在部隊時,定期有一輛車駛入軍區大院,攤開來賣書。郭鶴鳴買了一本《哈利·波特》,盜版大厚本,從魔法石到混血王子全有。他看了一遍,談不上熱愛,到2012年,他陸陸續續看完小說,去申請說這部書。他是不想再說傳統書了。
“老先生的道本、冊子,拿過來,故事我都吸引不了,就跟《紅樓夢》里史太君說的,逢公子必然落難,逢小姐必然招親,全這一套!”
“上頭”沒同意《哈利·波特》,說可能形成噱頭,還是說傳統書吧。郭鶴鳴本想作罷,但是,他的師兄弟李根說上了。郭鶴鳴覺得李根“說得敷衍,看不下去了”,并非深思熟慮,他開始說《哈利·波特》。
2012年7月21日,北京下起了至今仍令人聞之色變的暴雨,郭鶴鳴在德云書館,開說這部新書,他的開場也是一場大雨,外頭招牌名字寫的是《魔法石》。
那時的郭鶴鳴依然沒想著以后會指望評書吃飯,眼睜睜相聲來錢快,八個墊話攢一塊嘻嘻哈哈十幾分鐘就算一場,還總有觀眾買票;評書呢?全國光靠地上說書養活自己的演員,他幾乎想不出來。至今還是這樣。郭鶴鳴和鄭思杰都在學校里給孩子教課,貼補家用。
但越預備這書他越覺出好來。《哈利·波特》有偵探小說的底子,前后懸念設置得多,線索埋伏得遠,有點像傳統評書中的公案書,不同處在于公案書一早點明兇手,《哈利·波特》把懸念留到最后。郭鶴鳴是幸運的,他找到一個好的評書底本。
2013年初,《哈利·波特》第二部《密室》第一回已經在節目單公布,但前一天,場地老板臨時撤場,評書換成了相聲。
北京的書館大多慘淡經營。藝人們說,書座必得有錢有閑,清末書館在北京興盛,是因為拿著錢糧的八旗子弟沒事干,下午泡茶館聽書晚上泡戲園子就成了固定生活。解放后,先是許多傳統書不讓說,斷檔幾十年后電臺評書興起,在這種文化氛圍成長下的年輕人已經沒有了到現場聽書的習慣。再一則,在節奏快、壓力大的北京,如今“有錢有閑”的人有多少呢?
2014年,郭鶴鳴離開德云社。當年10月25日,距離《魔法石》結束過了一年零十個月,郭鶴鳴在新街口社區活動中心,開始哈利波特第二部,《密室》。這部書32回。2015年7月18日,開始說第三部《囚徒》,44回。2016年夏天,《囚徒》行將結束、第四部《火焰杯》初開之時,郭鶴鳴又失去了他的場地,甚至在馬連道一家只能容15個書座的茶館說過三回。也是在那附近,德云社“家譜”發布,他的八字評語“欺師滅祖手段卑劣”廣為人知。
2017年冬天,我第一次采訪郭鶴鳴,他穩穩地坐在椅子上,臉上有種被傷害過的戒備表情。往后的半年,我常去書館聽書,多次聽到郭鶴鳴和他的伙伴們用那八個字砸掛,或者說,它已經成為這個小圈子里重要的“梗”,每每引起會心的大笑。再采訪時,他的表情松弛了些。我的許多問題都在糾纏“用評書形式說外國書”,他總結道:
“書里主要還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你拿刀捅他一下他知道疼,只要理解了這個,就無所謂中國人、外國人,中國書、外國書。”

郭鶴鳴。由受訪者提供。
5
護國寺賓館古色古香,大堂一角豎著個大鳥籠,里頭一只大白鳥,時不時驚叫一聲。走過大堂左拐進走廊,兩邊墻上掛著老北京照片,在一扇永遠開半扇的防火門處上樓梯,再拐一個彎,門廊上掛著牌子,“護國寺賓館京劇票房”,里頭那間幾十平的小屋,鋪著團花紅地毯,擺了八張八仙桌,各帶四把高背椅,早上是賓館的外賓餐廳,每周三天是京劇票房,周五周六兩個晚上,便是評書小書場。六點半開,一般三人上臺,每人一小時多點。鄭思杰、郭鶴鳴、武啟深、武宗亮,四位平均年紀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在這里說書。
晚上八點五十,郭鶴鳴上臺,常穿灰色中式對襟上衣,肩膀西式做法,顯得板正,下著黑色水褲,白襪子,套黑色圓口布鞋。坐定,水杯放在左角,雙臂叉開按在腿上。說書人最好沒有太明顯的外觀特征,好隱在書后,不讓觀眾出戲。郭鶴鳴符合這個要求,就是這些年體重見漲,臉也見圓。他的圓臉上浮出笑麼絲兒的表情——笑意絲絲地漫在他的臉上。像是一個標志,他進入演出狀態,用話語營造一個中西交融的曖昧世界。
“細”是郭鶴鳴的追求,信息量得大,知識面得廣,郭鶴鳴把《哈利·波特》的世界鋪展開去,西方的神話,中國的星相學,英國史,魔法史,女巫的社會學著作,都是他的材料。有時候他從《哈利·波特》的世界里撕出去,拿出半小時批講中西方的民間傳說,他講過鳳凰,也講過蜘蛛,有人覺得這些“零碎兒”太多了,“不給書聽”。郭鶴鳴挺高興,“終于有人說我慢了。”按他的說法,前兩部一回書能占小說原文的三四張,到如今的《火焰杯》,一回書也就一張半的文字量。
聽過越多傳統書,越能明了評書《哈利·波特》的包袱。《囚徒》里,海格到三把掃帚酒吧救哈利波特,一通混戰闖出重圍,“改了趙子龍救阿斗了”;圣誕節假期之前校園里布置起來,五彩祥和多喜氣,“改了寶玉娶親了”。三位小伙伴去找海格,談他養的獅身人面龍尾首,跑了,沒人敢抓,郭鶴鳴仿著《君臣斗》里劉寶瑞先生的口風,“跑了沒罪,逮了——斬立決!”他還在評書里放了“彩蛋”,“哈利波特掏出魔杖,念了一段咒語”,說到此處,他抱起一早放在桌上的三弦,唱了起來。笑聲,掌聲。這些西方小說中的情節與中國曲藝的瞬時碰撞總能被他的書座捕獲,一種會心的笑,互文的笑。
外國小說的翻譯語言,傳統評書中的贊賦,各種曲藝種類中的腔調,在評書《哈利·波特》中交融。盧修斯在海格的房間看到鄧布利多,“校長先生,晚上好”,同時拱手作揖。鄧布利多答道,“夤夜至此,你找老朽有何貴干哪?”用的是京劇的腔調。哈利波特有時是個思維縝密彬彬有禮的英國男孩,有時,看著一碗復方湯劑想起豆汁焦圈——北京二環里子弟的那種紈绔范兒。《囚徒》最末,哈利波特在暗湖畔看到獨角獸,“頭至尾,長丈二,蹄至背,高八尺。頭上長角,肚下生鱗。”觀眾大笑起來,郭鶴鳴也笑了,“外國書別扭就在這兒”。
他努力讓這些復雜的元素顯得和諧,得意之處,譬如以小說為范本,把英國人的幽默變成中國人的幽默。赫敏設計一系列環節,讓三位同學變成斯萊特林的學生,書中一一列舉,“這麼多環節都會出錯”,可是中國讀者樂不出來。郭鶴鳴鋪墊了半天赫敏自以為得意的勁兒,先翻,“你覺得哪個環節會出錯?”再抖,“我怎麼覺得哪個環節都會出錯!”曲藝“鋪平墊穩”、“三翻四抖”的經驗被他拿過來,這是中國人的幽默,起碼是他的這些北方書座會懂的幽默。
《密室》和《囚徒》兩部,郭鶴鳴批講中西,常是撕出整塊,中西之間有個分界;到第四部《火焰杯》,他的跳進跳出變得更為頻繁細密。有些碰撞,聽書的人還沒反應過來,他已經說了過去。包袱抖響,觀眾挾裹在笑聲里,跟著郭鶴鳴的話語往前推進。聽得久了,在“外國小說”和“傳統評書”的密密交織里,好像也感受到了郭鶴鳴縫補的那個世界——不用過于在意所謂“違和”,郭鶴鳴自己也沒有那麼在意這個。
2016年7月23日,《哈利波特》說到第四年,郭鶴鳴上臺,先說了一會兒閑白。有些感慨。
“20多歲誰都雄心壯志,現在我是怕紅。最后一回《魔法石》,人比現在多,現在是什麼行市呢?等于我是從頭再來。前幾天看一知乎帖子,看我名聲還不算太臭,越發不想紅起來,就想守著這個幾尺小書臺子說書。”
他又回應了對他的若干評價,慢,摻水。在非演出狀態,他的笑容不多。
“有資格評價我的,取決于您手里的票根有多厚,因為這是買賣!”
“買賣”,一個江湖氣的詞兒,它提醒著評書原初的目的,得換錢。談及《哈利·波特》作為“新書”,到底郭鶴鳴也這麼說,“我們指著這個活著,都陽春白雪,不掙錢也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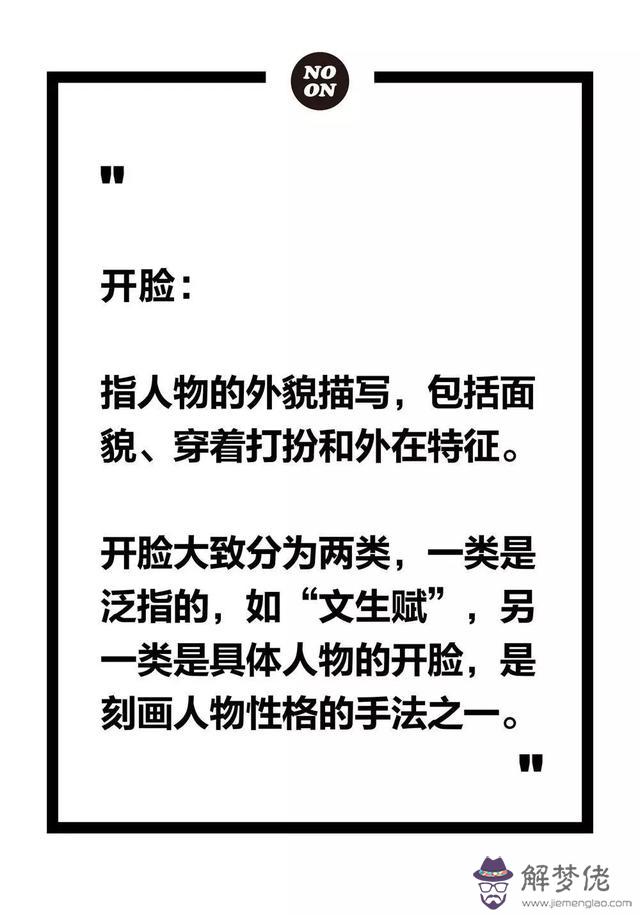
6
“鵪鶉蛋”是郭鶴鳴的老書座,她是北京人,比郭鶴鳴小幾歲,打小就跟著爺爺姥爺聽評書。2012年,她偶然看到了郭鶴鳴和他的《哈利·波特》。聽過第一回,發現郭鶴鳴不是按小說開頭,而是用羅琳后來更新的一段番外開場,鵪鶉蛋想,這是認真準備過的。她一路在網上聽了下去。
鵪鶉蛋是個哈迷,從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哈利·波特》的小說就開始看,光說這部小說,她自認了解不比誰少。但聽書到第13回,尼可勒梅談煉制魔法石,她發現評書里有小說沒有的東西。往后,“小說里沒有的”越來越多。
“他書渾厚的程度是最吸引人的”,鵪鶉蛋說,“就是他知道的或者為了這部書刻意去了解的,都放在里頭說。現在大家都有這個感覺,尤其要上班的人,生活節奏很快,每天壓力特別大,在這里就是個放慢節奏、汲取知識的過程。知識也未必有用,但確實可以豐富自己的眼界,多得到一些東西。”
《密室》開講,鵪鶉蛋打算到現場,看好了節目單買好了票,到了卻發現變成了相聲。那時,郭鶴鳴找書館場地而不得,隔了一年十個月才在新街口社區活動中心再說《哈利·波特》。鵪鶉蛋尋著去了,那是2014年底,“就覺得再聽視頻就不解恨了。”
“解恨”,就是這感覺。包括鵪鶉蛋在內的固定書座有十幾個,都是打小聽書,有如她一樣的哈迷,也有一些是郭鶴鳴還在德云社時期就喜歡他的。這些年他們風雨無阻,笑稱聽書就如上班打卡。郭鶴鳴是個說書的個體戶,小徒弟(就是在老舍茶館鄭思杰前頭說《水滸》那位)幫他檢票,媳婦兒幫他打理淘寶店,這些書座幫他看著錄視頻的相機,維持書館秩序。郭鶴鳴下場時也常問鵪鶉蛋一句,有沒有口誤的地方、漏掉的細節。
老舍茶館是個劇場,演員、觀眾截然分明。護國寺的小書館因為小,前頭說書,中間聽書,后頭候場的演員換衣服——太近了。但也是在這種親近里,和年輕的說書人一樣年輕的書座們部分建構了這些“新書”。
“新書”仍在嘗試,曲藝行當仍嫌寂寞。有一回,我坐鄭思杰的車從老舍茶館到護國寺去,他打開音響,是大鼓,他左手開車,右手在大腿上拍著拍子,嘴里學著鑼鼓音兒,這是京韻,這是鐵片,這是京韻大鼓上變調出來的滑稽大鼓。再問,他可能是滑稽大鼓唯一的傳人了,傳到現在,活剩了四塊整活,兩塊“半活”。
郭鶴鳴要學單弦,劉建云老師都不明白,你學這個干什麼?光彈,誰唱啊?起初還有個女孩唱,她爸是炸油條的,喜歡聽,非要女孩跟著劉老師學。女孩嗓子好,干凈沒雜音,就是一上課就張不開嘴,一下課就歡天喜地,騎車往外跑比郭鶴鳴蹬得還快。姑娘告訴他,不喜歡單弦,喜歡流行歌,喜歡潘瑋柏。一年后,這姑娘也不學了,剩郭鶴鳴自己彈弦。
時不時地,周五或者周六,我還到小書館去。這屋子胖子的數量明顯超過北京的其他地方,于是我也逐漸融入。書座前面坐著,說書人后面候著。到點了,袋子里掏出上回穿過疊好的大褂。疊大褂有一套專門的方法,折痕留在袖子外側,顯得立正。看一個人會不會疊大褂,也能看出有沒有師父傳授。曲藝行里把穿上大褂叫“挑上了”,挑念三聲,一個上揚的動作。
一個年輕的說書人挑上了。他一手握里頭是扇子、醒子和錄音筆的白手帕卷,從后排起立,往前頭走。經過一扇窗戶,簾子拉開一小片,黑夜使它變成一面鏡子,對著那鏡子他立了立頭頸,整了整衣領,抻了抻下擺,頂上像有股勁兒把他猛拔高一寸,扭頭轉身,他款步走上臺去。
—— 完 ——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文中說書術語,“道活兒”、“墨刻”由作者所擬,“開臉”來自1997年出版的 《中國評書藝術論》。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6045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