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劉家和
內容提要:關于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特點,從黑格爾到德里達,西方學界形成了一種偏見,認為中國沒有理性,沒有哲學。前輩中國學者在物質、制度和思想層面上都發現了中西文化存在著若干異同,但他們忽略了理性在中西文明中起到的作用。理性有不同的內容和類別。不同的理性類別組成不同的理性結構。雖然理性的爆發是軸心時代中西文明的共同特點,但它們表現出來的理性結構卻不盡相同。古代西方的理性結構包括邏輯理性、自然理性、實踐理性/道德理性、審美理性,但缺少歷史理性,其理性結構以純粹理性為主導,邏輯理性居于統治地位。中國的理性結構包括歷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有邏輯思想,但卻未發展出邏輯理性,其中歷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邏輯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維,歷史理性引領了中國的思維。這種理性結構的不同是中西思維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西文明之別,關鍵也就在于理性結構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邏輯理性占主導和中國文明中歷史理性占主導,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其部分原因則可溯源于各自語言之不同。語言特點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頭。
一、問題的提出
中西文化異同,在現象中隨時隨處可見。如果加以分類,一般可以分作:1)物質文化層面,2)制度文化層面,3)思想文化層面。從發生的角度看,每一前者對于其后者來說都具有基礎性的前提作用。從表里層次來看,每一后者都比其前者更為深入。因此,從交流與溝通的難易程度來說,每一前者都較其后者容易,每一后者都較其前者為難。思維方式屬于思想文化層面,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從中西思維模式異同的核心問題作一些嘗試性的探討。
中西思維方式的比較多年來一直是學術界所關心的題目,前賢們的耕耘使我們對中西之同異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下面簡單介紹一下他們的觀點。
王國維先生說:“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他又說:“吾國人之所長,寧在于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①
林語堂先生認為,與西方比較,中國沒有系統的哲學(systematic philosophy);中國重視實踐,重身體力行,不重形而上學;不注重邏輯,尤其不喜愛抽象的術語;中國重情,重直感,重安身立命,求可行之道。中西的不同,“可以說是直覺與邏輯,體悟與推理之不同”②。
唐君毅先生強調,中國文化不重視個人的自由意志;不重視理智的理性活動;不重視科學知識。“西方言哲學者,必先邏輯、知識論,再及形上學、本體論,而終于人生哲學倫理、政治。而中國古代學術之發展,適反其道而行,乃由政治、倫理以及人生之道。而由人生之道以知天道與性,而終于名學知識論之討論。”③
張東蓀先生在《知識與文化》中指出,與西方相比,中國哲學有三個特征:1)中國哲學不是西方的本體哲學(substance philosophy)與因果原則哲學(causal philosophy),而是“函數哲學”(function philosophy)。這種哲學強調自然與社會的“整體”(integral whole),注重變化和相互關系,認為個人在社會內如同耳目在人身一樣,“各盡一種職司而實現其全體”,君臣父子在社會上的司職與乾坤坎兌在自然界的司職是一樣的,都為的是整體。2)中國哲學不是形式哲學(form philosophy),因為中國人不分屬和種,沒有屬概念加種差的定義,不重視分類上的差異。3)中國哲學不追求“最后的實在”。由于中國人不重視本體,也就沒有實在(reality)與現象(appearance)的區分。“嚴格來說,中國只有‘實踐哲學’而無純粹哲學”④。
哲學史家張岱年先生列出六條中國與西方的不同:1)合知行。2)一天人。3)同真善。4)重人生而不重知論。5)重了悟而不重論證。6)既非依附于科學亦不依附于宗教。這六條與西方截然相反。張先生說,這六條中,他的前輩熊十力先生總結了三條,他自己增加了三條⑤。
前賢們從多方面分析了中西思維特點的不同,綜合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作如下的分類。在本體論方面,西方關注形而上學的存在,中國重視形而下的實在。宇宙論方面,西方追求萬物的本原,中國強調天人合一的整體世界觀。認識論方面,西方依靠思辨去掌握知識,中國依靠經驗性的體悟和直覺。邏輯方面,西方發展出邏輯學體系,中國則不予重視。倫理學方面,西方強調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中國專注于道德的實踐和人倫關系。根據雅斯貝斯的研究,中國和希臘在同一個時期內進入了“軸心時代”,以上各家的論述揭示了“軸心時代”的中國和希臘在哪些方面發展出各自的特點,他們的正確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理性在兩個文明中起到的作用。雖然理性的爆發是“軸心時代”幾個文明的共同特點,但是各個文明表現出來的理性結構卻不盡相同。本文認為,從“軸心時代”開始,中西的根本不同是理性結構的不同。
二、理性結構不同是中西思維不同的根本原因
(一)西方思維的理性結構
理性結構指由人類各種理性組成的體系,在這體系中理性的各個部分所起的作用有程度上的差別。理性(reason)有哪些部分?有純粹理性(pure reason)、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審美理性(aesthetic reason)、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和歷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純粹理性完全與人們的生活無關,是純粹的邏輯推理,概念的運用,其基礎就是數學、幾何學。邏輯理性的特點是可以進行邏輯演繹,一旦到了邏輯演繹,就脫離了時間,超出歷史理性的范圍了。實踐理性,柏拉圖不明確,亞里士多德講得很清楚,在他的《政治學》、《倫理學》之中,實踐理性最明顯的是道德理性(moral reason)或倫理學(ethics)。倫理學的希臘語詞根是ethos,有風俗(custom)或特點(character)的意思;道德(morality)的拉丁文詞根是mos,對應的英文也是custom(風俗)。自然理性是人們對自然界表現出來的規律的認識。歷史理性是人們對歷史進程的所以然和一定規則的探討和探尋,認識到歷史是“常”與“變”的統一:從“變”中把握“常”,從“常”中把握“變”。除此以外,還有審美理性(aesthetic reason)。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美的問題就經常被討論,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論述了美學。他認為,詩學所涉及的,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典型的、有概括性的東西,典型就具有一定的永恒性、概括性。西方哲學界比較晚些的時候,才提出來歷史有無理性的問題。西方人認為歷史沒有理性,是因為他們強調真理或純粹理性只有在永恒中才能把握。這一觀念可追溯到古希臘。可以說,古代西方的理性結構包括邏輯理性、自然理性、實踐理性/道德理性、審美理性,而缺少歷史理性,理性結構以純粹理性為主導。
希臘人的自然理性表現在他們的自然哲學中,他們也提出了類似中國“五行”的看法,水、火、地、風,后來亞里士多德又增加了以太。作為世界的本原,這些元素有單獨起作用的,也有兩個結合在一起起作用的,但都沒有很有說服力地解釋世界現象。雖然每一種理論都具有一定的經驗觀察和邏輯推理,但都沒有取得占統治地位的信服力,因此,到了巴門尼德,他另辟蹊徑,開創了抽象思維的方式。他指出,過去的這些本體觀點都是對自然的研究,都沒有觸及最根本的東西,沒有涉及永恒的東西,因為不論是水、風、地、火,都是活動的,而本原必須是靜止的、永恒的。永恒的是“存在/是”(being)。這是人類思想的飛躍,從此開啟以邏輯為根基的、抽象推理的哲學。中國五行相生相克理論是將共時性的東西變為歷時性的,循環性的,歷史性的,而且為政治服務;而希臘則將四種本原的東西保持在共時性范圍內。我們也許可以說,這與希臘沒有歷史知識的原因有關,也與巴門尼德個人阻止了“四大元素”歷時性理論的形成有關。
巴門尼德的存在/是有三個特征:第一是抽象,最高的普遍性;第二是超越時間,永恒不變的;第三是超越空間,在中國是,在美國是,在任何地方都是。這些特點就決定存在論不是歷史的,只能是邏輯的。到了柏拉圖,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柏拉圖在知識與無知之間,還重點分析一個東西,叫做“意見”(巴門尼德就提出了“真理”與“意見”的不同),有些意見是有意義的,但不具有絕對意義,所以歷史在柏拉圖看來就是意見。古希臘哲人包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否認歷史有理性。歷史則不被看中,因為歷史是變化的。人只能從永恒中把握真理,不能從變動中把握真理。
邏輯理性追求永恒的真理在感官世界之外,所以不能依賴感覺器官去把握,只能依靠思辨和分析的方法,自身演繹。幾何學用幾條自明的公理自我展開,演繹出定理,形成整個系統。A大于B,B大于C,A就大于C,永遠如此。三角形靠六個基本函數(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就可以研究整個三角學,不必出門去觀察客觀事物。閉門造車,出門必然合轍。希臘人認為歷史沒有理性,因為歷史是變化的,昨天是,今天也許就不是了,今天是,明天也許又不是了。要想把握一切,對象必須是永遠是,必須超越時間,就變成永恒的。“是”又必須是無限的,超越空間。這是從幾何學上講道理,所以柏拉圖說過:不學幾何學的人不能到我們這里來。亞里士多德也認為,研究本體存在的和研究公理的數學同屬一個學科。
西方的邏輯理性、自然科學與宗教信仰是有一定關系的。神/上帝,是人們從自然界發現的,或是從理性中發現的。蘇格拉底發現,人的五官安排得非常合理,從而判斷是被設計出來的,當然設計者就是神。亞里士多德的神是第一推動力的設想,解決了否則就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一直到17世紀,牛頓也仍然認為,靜者恒靜,動者恒動。是誰使動者動起來的呢?神/上帝,是最好的回答,上帝不做無用功。連康德這樣偉大的哲學家也無法在邏輯上否定上帝的存在。邏輯學建立在語言學上,把人的理性抽象為概念定義的內涵和外延,判斷,質的判斷,量的判斷,所有這些成為邏輯學。抽象的邏輯學建立后,人們都必須服從。從物理學角度和宗教角度說,希臘信仰神和基督教信仰上帝,是從邏輯上推出來的。也可以說,上帝依靠著邏輯而存在著。
希臘的歷史學也很發達,希臘人有沒有尋找歷史規律呢?答案是否定的。希臘的歷史學家是非常重視歷史真實的。為了把希臘與蠻族人的斗爭情況保留下來,希臘史學家必然追求歷史的真實;他們努力尋找當時參與事件的證人。希羅多德寫波希戰爭,他本人就親自參加了這場戰爭。修昔底德也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參加者。英文的History一詞,既有發生的意思,也有對所發生的事情記錄的意思。希臘人寫歷史也找原因,但是有局限。他們寫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時希臘都是城邦的觀念。進入城邦之前是黑暗的“荷馬時代”,那個時代的文字斷裂了,沒人能夠認識。那段歷史只是以神話的形式,恍恍惚惚地留存在《荷馬史詩》中,無法被書寫,也無價值。希臘的歷史學家看到的,只是當代的,他們不再注重神話了,而專注于人事,這是很大的進步。歷史僅限于當代,因此不容易總結規律,也沒有從“變”中求“常”。柯林武德指出,希臘的歷史著作只關心什麼是真實的。希羅多德使用的Historia一詞,在希臘文的含義是追問、考察,目的是強調對當事人或目擊者的追問和考察,重建事件的經過。
西方早期缺乏歷史理性的一個原因是經驗層面上的。在真正的希臘古代時代之前,有克里特島文明和邁錫尼文明,但都沒有留下歷史記錄和遺產。20世紀初,西方考古界發現克里特島文明的線形文字A和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B。直至1952年,英國學者溫特瑞斯解讀出線形文字B,始知這是希臘語。這是個了不起的發現,因為線形文字B與當今希臘語完全不一樣,中間沒有任何橋梁。而中國人解讀甲骨文則有很多橋梁可以借用,古今文字的演變有因可尋。多利亞人的入侵毀滅了邁錫尼文明,希臘進入所謂的“黑暗時代”。入侵者對前段的歷史沒有了解。《荷馬史詩》里敘述的邁錫尼時代的歷史,比如,特洛伊戰爭等,只是影子,對真實的歷史絲毫不知。導致希臘文明突然斷層的原因不太清楚,很多學者認為天災是個可能的原因。不管什麼原因,其結果是希臘人無文化傳統可以繼承和思考。從希臘作家的文字中看,他們幾乎不講過去的歷史,頂多是隱隱約約地提到一、兩句。城邦時代之前的文明沒有給希臘人留下什麼歷史傳統。
希臘的傳統是神話學。最初神與人是一樣的,即人格神(personified)。奧林匹斯山的神具有人的七情六欲,男盜女娼,狡詐亂倫。與人不同的只是超越了死亡。邁錫尼時代的英雄都是人神合一的,歷史人物與神分不清楚。作為文學作品,神話有其價值,《荷馬史詩》是文學經典。針對只有神話傳統存留的情況下,知識界就要問:什麼是人要掌握的知識對象?什麼是人應該認識的對象?答案是:自然。將自然而不是歷史傳統作為知識的對象,時間的維度立刻轉為空間的維度。中國的知識方向是歷時性的(diachronical),希臘的是共時性的(synchronical),與神話分離后,產生出人與自然獨立的思想,認識到人與自然是兩個不同的類,所以希臘哲學始源于自然哲學,物理學(physics),逐步發展出邏輯理性,并且占統治地位。
(二)中國的理性結構
我們同樣從經驗層面上看中國的情況。雅斯貝斯談到的“軸心時代”在中國是春秋戰國時期,在希臘是城邦時期,在羅馬也是城邦時期。為什麼軸心時代會發生在這一段時間?雅斯貝斯的解釋是:發生在兩個帝國之間,人們有一個“自由呼吸之際”,英文是pause for free breath。有的翻譯是:為自由而暫停,其實準確的意思是:喘氣之際,不是停頓,德文與英文都很清楚。這樣的關鍵詞句,看中文版之外,一定要看德文英文。希臘在“軸心”之前有個波斯帝國,但這個帝國是虛擬的;中國之前有三代時期。從經驗層面上說,周人取代殷商時,不是將商人完全殲滅,徹底去除,而是進行了很好的繼承。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說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中國的歷史記載非常豐富,而且古今是連在一起講的。《左傳》中的人物講當代,離不開古代,拿古代的事情驗證當代。古代文獻中最典型的一句話就是周公在《尚書》中說的“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多士》),先周時期甲骨文的發現證實了周公的說法。克商之前的周人已經繼承了殷文化的很多東西。這表明中國人在文化文明上是有根底的,一脈相承的。有因循,有損益,也就是有繼承,也有改變。這就是中國歷史理性得以建立的直接的經驗基礎。歷史就是有、無的交替和延續。有會變為無,無也會出現有。“變”與“常”,可以用旅客住店來比喻。旅客昨天來今天走,都是過客;而旅店是常的,昨天和今天是不變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也是同樣的意思,營盤是“常”,兵是“變”。
周公沒有否定所有的殷王,只是否定商紂王,紂之前的都被稱為哲王。這就是繼承的原因。另外,周公告訴人們一個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就是改變,是非常偉大的思想。周公的時代可以看成中國的“前軸心時代”,孔子所處的“禮壞樂崩”的春秋時期是“軸心時代”。周公只意識到統治者要實行德政,但沒有提出“仁”的概念,這是時代的局限。周公面對的是建立各種制度的要求,考慮的是如何穩定局勢。孔子繼承周公的道德觀,發展出“仁”的觀念,即把人當人對待。這一觀念的偉大程度,接近自然法。
中國歷史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原因是,哲學家們離不開傳統。中國最初的歷史理性是與道德理性結合在一起的,即周公的言論,但到戰國時被五行理論取代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從漢到隋,一直成為政治哲學的核心,因為關系到政權正統與否的問題。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傳統,這既是遺產,也是包袱。后來的人背著這個大包袱,不能將其輕易甩掉。孔子何嘗不是背著個大包袱向前走?他的思想有新有舊。先秦諸子各家都有對三代的繼承,都“出自王官”的說法不可信,但都有傳統的根源。儒家墨家都引《詩》、《書》,只是解釋不同。儒家溫和地繼承周公的觀點,孔子的倫理是有層次的,由里向外是“仁”,由外向里是“禮”。墨子的兼愛沒有等差,有點類似基督教,但又沒有基督教的整體理論。道家否定“六經”,當然否定的時候,就會產生黑格爾說的“揚棄”。法家也否定“六經”,但對其內容也很熟悉。“六經”的特點是“經世致用”,是政治哲學,是倫理哲學。《孟子》受其影響,講些經濟理論,法家也提出自己的經濟理論。司馬遷引其父親司馬談的話,“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見,歷史理性與政治掛上了鉤,史學為政治服務,為實踐服務。歷史既然與時間有關,就是線性的,線有直線和線段。直線的兩端沒有限制,可以無限延長;線段的兩端都有頭,不可延長。中國史學有“通”的精神,可以比作無盡頭的直線;古希臘羅馬的史學只關注當代,可以比作線段,線段也是直線,只是長度有限。
中國的自然理性不如希臘的發達。“五德終始說”是歷史理性與自然理性的結合,用五行的循環比附朝代的更替。這種比附的結果,秦國毫無顧忌地、公然地使用殘酷的暴力手段,實行專制獨裁,他們認為這是完全合乎歷史規則的,有歷史的合法性。到了漢代,儒家感到秦的殘暴違背道德,改“五行相克”為“五行相生”,并且把秦排除在相生的序列中,不承認秦為正統。所謂的“紫色蛙聲,余分潤位”,意思是說,紫色是雜色,是紅與藍的混合,不算正色,蛙聲不算正聲。余分的概念是,太陽運行一周的時間與月亮盈縮的時間不能整除,一個月多出來一、兩天的叫做大余,多出幾個時辰的叫小余。所有的余積累到29天或30天就可以閏月,所以叫“余分潤位”,即歷法上,歲月之余分只能算是潤統,而不是正統。、這是《漢書》形容王莽篡政的話,但也適用于秦朝。
周公講的天是宗教之天,天是主宰,有道德,挑選人間最有德的人做統治者。孔子講天,對挑選決定人王的宗教之天存而不論,將道德之天引入人心。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產生一個后果,即人可以與天、地參,給后來發展出的天、地、人“三才”鋪墊了道路。荀子講天,又不同于孔子,是自然之天,但他不是討論自然,研究自然。他公開聲稱“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此觀點極其壯觀,但他沒有說應該研究自然,分解自然的成分。可見,中國人從來沒有將天/自然當做一個課題來研究。人為萬物之靈,天與人就是一致的。孟子認為,知人就可以知天。這一點到了宋儒那里,就更加大談特談,而那時西方的文藝復興已在萌芽中。儒家講“因循”,講“損益”,就是要去包袱,批判地繼承。但是在文化傳統如此深厚的條件下,很難使“損益”達到質變。沒有外在因素沖擊的話,很難有突破。佛教進入中國,但很快就中國化了。人是歷史的動物,即人是擺脫不開歷史傳統的。古希臘文明的傳統是空白,也就沒有包袱在身,可以輕松而自由地進行思想活動。中國三代甚至遠古帝王的傳說和歷史是極其豐富的。這些傳統使軸心時代的思想家無一不重視歷史,可見他們受到傳統的影響有多深。
綜上所述,理性有不同的內容和類別。不同的理性類別組成不同的理性結構。理性是多重的,中西理性的側重點不同:西方重視邏輯理性,中國偏重歷史理性。中西文明之別,關鍵在于理性結構的不同。西方人,包括黑格爾,認為中國人沒有理性。實際上,中國人有理性,只是結構不同。中國雖然沒有邏輯理性,但也有一定的邏輯思想,而中國是歷史理性占支配地位。中國人重視歷史理性,但沒有從歷史理性中推出邏輯理性。西方的歷史理性從分析中來;中國的是從經驗中以歸納的方法獲得的,在“變”中發現“常”。中國人看待“常”是離不開“變”的,即“常”與“變”的統一。這兩類理性對人類都有貢獻,缺一不可。
(三)邏輯理性、歷史理性、道德理性三者的關系
理性結構主要包括了邏輯理性、歷史理性和道德理性,那麼,它們之間是什麼關系呢?我們先分析邏輯理性與歷史理性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歷史理性與邏輯理性有強烈的互相排斥的力量。這是因為,邏輯理性從概念開始,概念有抽象的過程,有超越時間、空間的特征,明顯地排除了歷史理性。歷史理性是離不開具體時間、空間的。我們讀《論語》發現,孔子對“仁”就是不給定義,這不是孔子無知,而是為了因材施教,對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解釋。給出具體的定義,發揮就被束縛住了。也就是說,歷史理性很難融入邏輯理性。西方邏輯理性發展出“在場的形而上學”,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幾何學就是由在場的形而上學建立起來的。給概念定義的時候,一定要說某某是什麼,不是什麼。所不是的東西就退出去了,就不在場了,剩下的就是在場的。隨著定義的深入,退場的越來越多,分析就達到最細致的程度。
柏拉圖通過概念由低向高、逐漸由特殊到一般的發展的方法得出最高的型相。每向上一層,就抽象一次。抽象到最后就是存在,這個抽象的存在就脫離了時間和空間。脫離時空就與歷史無關,因為歷史必須是發生在時空中的。巴門尼德的存在與非存在,二者絕對分離,所以無法發展運動;到柏拉圖的通種論就可以運動了,是邏輯概念的運動;黑格爾的《小邏輯》也是概念的運動發展,而不是經驗事物。邏輯的發展是歷史的,這是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的交叉點。反過來講,歷史理性中有邏輯。但是,在根本上,二者是排斥的。
第二方面,既然歷史理性與邏輯理性都屬于人類的理性,二者之間就有內在的不可分割性,也有互相滲透的特點。從邏輯理性方面論證,我們可以問兩個邏輯學方面的問題。一問:邏輯理性是不是人的理性?答案是肯定的,邏輯理性是人具有的,不是別種動物的。再問:邏輯理性是不是人的全部理性?答案是否定的,邏輯理性只是人類理性范圍中的一種。上面兩個邏輯學的回答是兩個判斷,第一個判斷不周延,第二個周延。邏輯理性是人的理性,在人的范疇之內,不周延。邏輯理性不是人的全部理性,“全部理性”是周延的。這兩個判斷表明,人和人的邏輯還是歷史的。人有出生、成長、衰老、死亡的歷史。在西方,到黑格爾時期,他已經意識到邏輯本身就是歷史的,因為從柏拉圖的通種論開始,概念就在歷史演變中,邏輯的發展最后是數理邏輯、符號邏輯。黑格爾說的“哲學就是哲學史”,他的《小邏輯》講的是概念發展的歷史。西方的形而上學也是形而上學史,邏輯學也是邏輯學史,都是人的,都是歷史的。邏輯理性,并不是希臘人建立以后就不再變化了,后來的邏輯學不僅不斷發展,而且有不同的學派。符號邏輯至少就有四個發展階段。也就是說,邏輯的東西仍然是在歷史之中。
培根指出,人天生有三個功能:有理性,所以產生邏輯;有情感,所以有詩歌;有記憶,所以有歷史。這是講人的存在功能,屬于本體論哲學,這一觀點非常重要,給予史學一個合法的地位。歷史和邏輯的關系是緊密的,歷史理性受邏輯理性支配。人之所以成為人,是有理性思考的。人與人對話,只有符合邏輯才能交流。海德格爾說語言是人與生俱來就存在于其中的東西,人不可能離開語言而存在。語言必須有起碼的邏輯才可以成為人際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說,人離不開邏輯。一篇文章寫得好,對讀者來說就是對話,讀者聽到覺得是合情合理,合理就是合乎邏輯。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時間地點人物景象,敘述層次分明,邏輯關系十分清楚。你不能把夏天的景象寫成冬天的,冬天的景象寫成夏天的。你不能說早飯你吃了,又說沒吃。杜牧的《阿房宮》描寫秦造阿房宮的鋪張奢華和百姓的疾苦,最后得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結論,并且表達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這一真知灼見。文章前后的邏輯關系和卓越的歷史理性使世人贊嘆不已。中國古代的博弈、運籌、兵法,等等,都有邏輯在其中,邏輯就在人的生活中潛藏著。亞里士多德的“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就指出了人的定義。對歷史的考證,必須依靠邏輯。史書中前面說有某事件,后面說沒有,這時就需要依據其他方面的材料進行邏輯推理來決定有無。
以“空城計”的故事為例。《三國志》沒有記載諸葛亮的“空城計”事件,但這個故事在南朝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就有流傳。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認為《三國志》太簡單,命令裴松之搜尋各類材料補充《三國志》。裴松之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有150多種。其中有本書提到司馬懿的后人與朋友對話,朋友說到了空城計的事件,并且以此事件嘲笑司馬家族。裴松之從幾個方面分析,質疑這個故事的可信性。“空城計”的故事說是發生在西城,在陜南的東部,現在的安康一帶。當時漢中和關中是主戰場。諸葛亮在漢中,出祁山伐曹魏,先向寶雞方向出發,然后從渭水上游向關中西安發動進攻。當時曹家不信任司馬懿,讓自家人曹真駐守關中,而司馬懿的部隊在當今的湖北一帶,所以西城的地理位置與“空城計”對不上,司馬懿也不在關中。曹真曾經計劃主動進攻諸葛亮,從關中進入漢中,但是在路上遇到大雨,惡劣天氣將近一個月,曹真也因此生病。這時,曹家才將司馬懿調回關中。所以司馬懿與諸葛亮在西城的對抗,沒有可信性。
中國史學是有邏輯的,但中國人沒有將邏輯抽象地發展出一套有定律有系統的學科,而習慣于具體的形象思維。先秦諸子論證其觀點時,都是引用具體的歷史事件,司馬遷引孔子語“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道不離器”的說法表明,“道”本身不能推演,必須依靠具體的事物“器”來解釋。中國人所依靠的邏輯主要是歸納法。西方人則認為,歸納法是不可靠的,你可以舉出一萬個例子,但找出一條相反的例子,結論就不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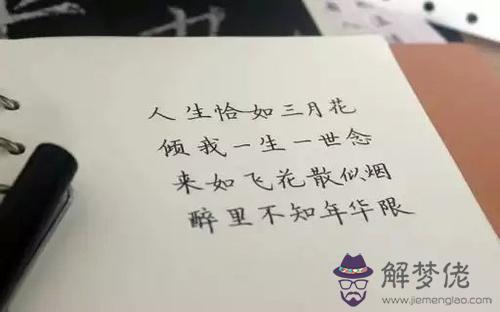
史學離不開邏輯,材料的取舍和甄別等等,都要經過邏輯的推理。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又是相互聯系的。邏輯理性直接影響到自然科學,歷史理性影響到人文學科。而自然科學本身也是歷史的。邏輯理性對歷史理性來說,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沒有邏輯理性,就沒有歷史理性;但是,有邏輯理性不見得就有歷史理性。為什麼如此?因為人作為一種動物,有非理性的方面:七情六欲。感性、情感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德國哲學家狄爾泰提出的“體驗”(erleben)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感情這東西,動物也具有,但動物沒有邏輯理性。邏輯理性與歷史理性,前者以推理為主,后者以感性為主。單靠邏輯,沒有經驗,是不行的;單靠經驗,沒有邏輯,也不行。英國從培根開始,二者結合,出現了工業革命。
我們再看邏輯理性、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倫理學)的關系。倫理學也是一個專門的學科。歐洲有個學者,后來去了美國,叫麥金泰爾(A.Maclntyre),寫了《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研究道德理性。他不僅研究西方的,也研究中國的。道德理性自古就有兩種。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認為,“知識即美德”。知識決定道德,知道什麼是善,就會行善。在蘇格拉底看來,道德是由邏輯理性決定的。亞里士多德不同意老師的觀點,他的《倫理學》強調道德由風俗決定。風俗有時代的不同,地區的不同,道德觀是不同的。所以,亞里士多德的道德觀是歷史的。康德認為,道德一定以理性原則為前提。“金律”(Golden Law)也是歷史的,古今貫通的;也是隨時間推移而變化的。一些古人認為符合道德的東西,現代人則認為不符合。中國人認為符合道德的,外國人認為不符合。宗教極端主義分子和恐怖分子的道德觀也與其他人不同。不同道德觀的人,在歷史舞臺上都受到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之光的照耀。蘇格拉底的道德觀是邏輯理性,亞里士多德雖然強調邏輯理性,但他的倫理學卻是歷史理性。文藝復興時期的拉斐爾在梵蒂岡教皇宮里創作的《雅典學院》,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二人放在畫中央,柏拉圖手指向天,亞里士多德手指著地,表現出師徒二人的理論不同。
凡是認為古今道德是一律的,就是邏輯的;凡是認為道德可以繼承可以變化的,就是歷史的。我們可以說,道德理性既有邏輯理性的依據,也有歷史理性的依據。在邏輯理性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道德理性受其支配;在歷史理性主導的情況下,道德理性也必然受其影響。中國的倫理有古今相同的道德,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隨時代變化,有邏輯理性的背景;中國倫理也講前后變化的道德,這集中體現在“禮”的層面上。孟子認為,“男女授受不親”,是符合道德的,但是,見嫂子落水而不去援手相救,“是豺狼也”,這種情況下,“男女授受不親”的規矩可以不遵守,這叫做“權”,即權變。權變,就是以非正常的手段達到正常的目的。中國人現在認為男女跳交際舞,道德上沒問題,已經放棄了“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可見,道德理性反映了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
在中國,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周人的天命論開始,古典文獻中充滿了統治者必須以德治國才能夠長期執政的看法,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三皇五帝的憧憬,更是把三代由天命論決定王朝命運的歷史推向烏托邦式的遠古時代。《春秋》作為史書,也是為了經世致用而作。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下》)體現了歷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結合,他所推崇的“王者”是實行“仁政”的君主。
道德能不能繼承?這個問題中國曾經討論過,是以批判的態度對待的。無產階級怎麼能繼承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道德?可是,以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對傳統道德應該批判地繼承,這也是黑格爾的否定中的繼承。批判繼承,既是邏輯的,又是歷史的。邏輯在道德上有合理性,道德怎麼能沒有繼承呢?剛出生的嬰兒,無法以道德觀去衡量,他一出生就在承受著歷史的包袱。中國古代,男女如果沒有媒人,怎麼能結婚呢?現在則無所謂。可見,不同時代,道德標準不一樣。男女授受不親,當時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國人對西方男女見面相互貼臉的行為,是看不慣的,認為不符合道德標準。大清王朝的使臣見到這樣的行為,驚嚇不已。現在則不同了。道德是由風俗決定的,一點不假。
人必須有歷史理性,也必須有邏輯理性。邏輯理性也好,歷史理性也好,對人都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這一點在歷史中得到了證明。這兩種理性各自都可以在不同的文明中占據支配地位,其他理性占從屬地位。
(四)歷史理性與邏輯理性的作用
世界歷史,在科學革命之前,中國一直處于優越的地位,而西方處于落后的地位。因此,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著名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革命?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原因是中國重人事的歷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而西方以邏輯理性占統治地位。可以說,西方人“醒來”早,而“起來”晚。古希臘以邏輯理性為基礎的幾何學、數學、自然學,在當時沒有什麼實際用處,所以長時期內是學者為了純學術而研究的對象。直到17世紀,邏輯理性才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決定性的方法。法國的笛卡爾將幾何學和數學結合在一起,創立了解析幾何,引入了坐標系和線段的計算方法。這一貢獻的用途非常大,比如,可以計算拋物線。英國的經驗主義者培根和其他幾位哲學家兼科學家提倡科學研究應當是理論和實驗相結合,這一方法在科學領域也有極大的貢獻,開啟了工業革命。培根的經驗主義是建立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之上的,除了分析判斷以外,又加上綜合判斷,西方走到了前面。培根的書名《新工具》,就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工具篇》,兩人同等重要。一切科學學科,包括研究微觀世界的量子力學,都是以嚴密的數學邏輯為基礎的,每條定律都有相應的數學公式表示。沒有邏輯就沒有科學。
歷史理性的作用表現在社會層面。現在產生文明沖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風俗不相容。如果依賴邏輯理性來解決文明沖突,必然產生更嚴重的沖突。歷史理性是法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如何證明?羅馬帝國時期的近東、中東,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教之間,甚至各個教本身內部,有著尖銳的矛盾沖突,甚至發生多次戰爭。任何一個溫和的教派,在受到壓制時,都有可能發展為原教旨主義。歷史理性關注人的情感,強調“變”中有“常”,尋求歷史所以然,因此能夠引導人們設計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人類既然有非理性的一面,就不能僅以邏輯理性來處理矛盾。韓國人與日本人有很大的矛盾,這就是歷史造成的。如果沒有歷史理性,我們就不容易理解歷史。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但不是純理性動物。宗教人士認為純理性的只有上帝,非宗教人士認為純理性的人如同計算機,失去人情味。也就是說,人除了理性之外,還有感情,所以人的行為不全由理性支配,在很多情況下,感情支配人的行為。理性與非理性,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分析過了。他們認為,人的靈魂中大致有四個部分,有的屬于理性,有的是非理性。先秦儒家也提到這方面的問題,性善性惡即是,但他們的分析沒有希臘人充分和徹底。
人性的善惡或人的靈魂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問題,歷史理性能夠理解,而純粹的邏輯理性則不能。正因為如此,人類歷史才有偶然性,而以邏輯理性推之,歷史則沒有偶然性,全是必然的。說“人心叵測”,“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按常理出牌”,都是明顯的例子。人在作決定時,往往有“不在場”的非理性因素在后面起作用。歷史必然與偶然的問題可以從這兩類理性的作用予以回答。邏輯理性必須歷史化。幾何學的論證,不需要結合事實,僅僅是一條一條地推導,就必然得出結論,沒有偶然,數學概率論才有一定的偶然性,這是因為概率論結合事實了,歷史化了。
西方嚴格的邏輯是排中的,非彼即此,這樣易于導致強制別人,不結合實際情況。這是今天中東動亂的原由之一,也是“阿拉伯之春”造成一片戰亂的因素。“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排他的。世界需要包容性,需要多元化。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是包容的,是適合人類的,是“金律”。基督教有包容性,但歷史上暴力不斷。人類在進步,現在的基督教好多了。
邏輯理性在永恒中求真理,歷史理性在運動中求真理。運動中何以能夠求得真理?因為運動是“常”與“變”的統一,“常”中有“變”,“變”中有“常”,無“常”就無理性可言,真正的歷史就是“常”與“變”的統一。這是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概念上的根本區別。人怎麼能不是歷史的呢?人總是有生有死,不可能像上帝一樣是永恒的。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相互排斥。邏輯理性從抽象開始,一抽象就超越時間,超越空間,歷史就被甩出來了。歷史則就在時間空間中。
我覺得,倫理學能夠成為理性的,已經是實踐理性了,而歷史理性不過是實踐理性的一種。倫理學有從邏輯理性推出來的、固定不變的規則,適用于任何時代和地區,比如,康德的“絕對命令”和“人就是人,而不是達到任何目的的工具”,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倫理學也有歷史理性的內容,比如,由于風俗的變化,過去符合道德的行為,后來不符合了;過去不符合道德的,后來符合了。馮友蘭先生曾提出道德可以“抽象繼承”的說法,這個觀點很矛盾,道德到底是蘇格拉底的“知識說”呢,還是亞里士多德的“風俗說”?風俗是變的,而邏輯理性的“知識說”是不變的。麥金泰爾的倫理學,也涉及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
西方思維走向抽象的道路,一旦抽象,就超越時間空間。抽象時舍去具體的東西就不在場,留下的是在場的,是一種抽象的在場,是永恒在場的,所以叫做“在場的形而上學”。抽象的方法是為了舍去現象,探究本質。只有通過不斷地抽象,不斷地進行定義,不斷排除在場的,數學和其他科學才能夠發展出來。在場形而上學對人生沒有什麼用,簡單的邏輯學對人生還是有用的,到了數理邏輯的高層次就沒什麼用了。科學方面的數碼技術對人生的影響很大,從照相機到電腦,都是革命性的。20世紀的存在主義哲學流派就批評在場的形而上學,海德格爾追求的存在,不是在場的形而上學的存在,而是要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存在主義者認為,在場形而上學否定了存在主義所追求的“存在”(existence),即人的存在。
每一個人自身不全是理性的,人與人結合成群體,非理性成分就更多了,許多事情的處理,是不需要邏輯理性的,可能性就夠了。比如夫妻,一個是南方人,一個是北方人,吃米吃面的問題很難避免。解決這樣的生活問題,邏輯理性是沒有好的效果的。歷史不像算命可以預知將來,歷史有不可預測性,但是,不可預測之中,有沒有可以預測的?傳統中國的史學回答:可以。人們可以從歷史發生過的事件引以為鑒,可以通過時刻調整達到理想的歷史目標。
這一節分析了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認為所有方面的不同可以歸結到理性結構的不同。邏輯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維,歷史理性引領了中國的思維。
三、二分法的不同是理性結構不同的根本原因
思維方式的根本不同,不少人傾向于從社會生產方式和地理位置上去尋找答案,比如,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商業和航海業發達,人們的特點是開放性,而中國是農業社會,人們安土重遷。生產方式和地理環境方面的解釋不是根本的,歷史的資料也不足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前面提到的希臘和中國在前軸心時代留下的歷史遺產的多寡不同也是一個原因,但這些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我們應該從人類思想起源方面尋找,其主因是思維的“二分法”(dichotomy)的根本不同。
我們如何能夠知道人類最早的思想方法?知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可以回答,只有從邏輯上去尋找答案。人類最初狀態是混沌的,這雖然沒有任何歷史根據,但傳說中有。中外都經歷過一種混沌的狀態,英文是chaos,是一無所知的狀態。最初的知識是一分為二觀念的產生,一個分成兩個的觀念。中國的神話“盤古開天辟地”講的就是一分為二,天地之分。老莊也講混沌。《莊子》講南海之帝、北海之帝為中央之帝混沌開竅,一日鑿一竅,七日鑿七竅,七竅成而混沌死。這反映了認識是從區別產生的,沒有區別則不能有認識。孩子最早認識的是父母,媽媽爸爸的發音mama、baba,在世界上是通語,因為都是唇音,發音最容易。假如沒有比較,那麼我們所面對的就只能是一片混沌。人類認識的真正起點只能是混沌的二分。視覺之區分光明與黑暗,聽覺之區分安靜與喧嘩,嗅覺之區分清香與惡臭,味覺之區分鮮美與苦酸,觸覺之區分柔軟與堅硬等等。一切感性知識皆由此開始。在康德的認識論體系中,在感性認識階段作為先驗的直觀形式的時間與空間,是以比較的形式呈現的。在知性認識階段作為先驗的十二范疇(分為四組)也無不以比較的形式而呈現。甚至進到了他的理性認識階段,他覺得出現了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Antinomy,也分為四組),至黑格爾則以“存有”(Being,Sein)本身就包含了矛盾來加以解決。所以,康德的“二律背反”也是以一種比較的形式呈現的。比較既是一切作為認識對象的存在的基本屬性,也是認識本身的基本屬性。因為人類認識對象與人類認識主體的基本屬性統一,所以對于真理的認識是可能的。從邏輯上說,人的知識絕對是從一分為二開始的。
希臘哲學史上最早采用二分法的是畢達哥拉斯,他的有理數與無理數,就是二分法。無理數被排斥在有理數之外,因為二者之間不可通約。二分法在數學上的作用正是邏輯理性的體現。幾何學也建立在二分法基礎上。幾何不能有矛盾,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畢達哥拉斯以后的哲學二分法是存在與非存在之分,存在就是有理的,無理的就不能存在。比如,巴門尼德的存在與非存在之間絕對排中,非有即無,非無即有。凡是存在的就是知識,是能說和能想的知識;非存在不能說不能想,不是知識。存在是一,而不是多。柏拉圖的“分有說”,將存在從一發展為多。一個“我是”就分成兩個,一就變成多了。不能動的“是”變成可動的。“我不是”包括了“是”。這個動,是觀念的運動,不是歷史的運動,不是歷史理性。歷史理性是人的運動,而這只是概念的運動。然而,概念的運動,一分為二,突破了靜止的觀念,在思想上是非常有意義的,涉及到辯證法。西方的二分法對科學絕對有好處,當今的數碼技術帶來的革命,的確離不開二分法。
柏拉圖運用兩分法來尋找定義,先將一個普遍性的概念分出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從二者中選出一個有關的概念再進行兩分,重復這樣的過程,最后得到定義。比如,“政治家”的定義先從“管理一群動物的技藝者”這個概念開始,將其分為“管理野蠻動物者”和“管理可馴服動物者”兩個相對立的概念;然后將前者“野蠻動物”排除,對后者“可馴服動物”繼續進行兩分,得到“管理水生動物者”和“管理陸生動物者”;后者再分為“管理飛行動物者”與“管理行走動物者”;后者分為“管理有角動物者”和“管理無角動物者”;后者包括“管理可雜交動物者”與“管理不能雜交動物者”;后者有“管理四足動物者”和“管理兩足動物者”;后者包括“管理有羽翼動物者”和“管理無翼動物者”。將每一層的兩分中保留下來的那部分加在一起,就得到了“人”的定義。因此,“政治家”的定義就是管理一群可馴服的、陸地生活的、行走的、無角的、不能雜交的、兩足的、無翅膀的動物的人。這一定義雖然不準確,但其邏輯的定義方法是奠基性的。更加嚴格的定義,是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屬概念加種差”(genus+differences of species)。
西方的二分法,永遠是除外法:規定一次,就否定一次。規定了“管理無角動物”,就將“管理有角動物”除外了。斯賓諾莎的“規定即否定”的深層含義就在這二分法之中;牟宗三先生也說:“一有抽象,便有舍象。”每抽象一次,就會抽出共同的東西而舍去特殊的東西。所有“A是什麼”這類的命題,同時也說明“A不是什麼”。比如,“你是”,就是“你是你自己”,意味著“你不是非你”,將不是你的人排除了,這才真正把“你”講全面了。“你是人”這樣的判斷表示,你不是非人,但因為大家都是人,“你”與別人分有了“人”這個概念。這兩句話在邏輯上把一個“你”分成了兩個“你”。
二分法和思想律是全部邏輯系統的基本原理。二分法體現了邏輯的對偶原則:任何一個項A被否定后就成為它的相反項-A,-A被否定就成為它的相反項A。比如:有理數的否定就是無理數,反之亦然;存在的否定是非存在,反之亦然。存在好理解,非存在就不好理解了,在現實中沒有,但它的意義是邏輯上的,邏輯的威力就在于它可以超越感性的認識,在純理性中不違反定律的要求。肯定和否定的對偶性是思想律的根本。二分法的關鍵在于與三條思想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緊密相關。一個概念在被兩分之前,自身就等于自身。公式是A=A,不能不是A。這是同一律。兩分之后的兩部分之間的關系必須是相互排斥的,非彼即此。用判斷句表示就是:凡S不是P,凡P不是S;公式:A×(-A)=0。如果有的S是P,或有的P是S,二者的關系就不是相互排斥的。這是矛盾律。一個概念一分為二后,兩部分加起來必須是窮盡的,必須還等于一,不能有遺漏的部分。用判斷句表示就是:凡非S是P,或者,凡非P是S;公式是A+(-A)=1。這是排中律。
中國的是《周易》的兩分法,即陰陽魚、太極圖式的。陰陽是互補的。男為陽,女為陰,男女結合生子,繁衍后代。因此,由陰陽而八卦,由八卦而萬物。陽卦中有陰,陰卦中有陽。西方的兩分法,1里面的A和—A不能運動,《周易》的陰陽是可以運動的,但運動的規則缺乏邏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二者不是排斥的,也不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沒有劇烈的斷裂。《周易》的二分法,被排除的東西又進來了。乾坤沒有定義,在這里是天地,在別處是牛馬,是父母,等等。乾坤永遠在場,因為舍象沒有舍出去。母親生了兒子,陰(母親)就應該退場了,只剩下陽(兒子)。這與西方的不同。西方每一層的抽象,都將一部分舍掉。說到茶杯時,所有茶杯的概念就在場,非茶杯之物就被舍掉,或退場了。抽象的結果到“是/存在”的時候,就是永遠在場。
畢達哥拉斯以數為萬物本原,《老子》也講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用數來解釋。可是再往下,就沒有數了,而是象。以后的思想家將數發展為術,即《易》中的象與術的結合。比如:六、七、八、九,老陰、少陽。三陽為老陽,三陰為老陰,二陽一陰為少陽,二陰一陽為少陰。“大衍之數五十”的“數”不再是《老子》“一生二”所講的數了。其結果就是沒有往抽象的方向發展,象術都是現象界的和具體的事物。《老子》提出“道”,沒有進入“非道”的理路去討論。
《周易》從陰陽兩分開始,但沒有繼續沿著兩分的道路向下走。八卦是陰陽兩極產生的結果。乾坤為兩個門戶,進入后,應該二分為四,但沒有繼續兩分,而是用三分來組合。在乾坤兩卦之下,三個陽卦,三個陰卦。為何兩個陰爻一個陽爻的卦屬于陽卦?王弼認為,天地人三才,做主的只有一個。王弼注《易》,已經排除了很多漢代的“術數”非理性成分,但他的理性仍然不夠徹底。他的“三才”說不對,三應該代表三個階段。人類早期,觀察到一切東西都有發生、發展、衰亡三個階段,一、二、三這三個數可以代表每一天早中晚的現象和人類少年、中年、老年的現象。如果從陰陽繼續二分的話,就無法表現三個階段的觀念。佛教講生、老、病、死四個階段,其實主要還是三個,合病與老為一個階段。天地人三才是橫向的分法,三階段是縱向的分法,這符合早期人類對事物觀察有三個階段的認識。陰陽是觀察事物得出來的兩個相關的觀念,光明與黑暗,白天與夜晚,太陽與月亮,男與女,等等。同樣,三個階段的觀念也是觀察的結果。說“天垂象”,“觀天象”,就是這個意思。
基于白天黑夜的陰陽觀念,發展出早中晚三階段的觀念,這就是從二發展出三的走向,異于西方的兩分法走向。有了早中晚的時間觀念,陰陽的發展和變化就成為可能的了。有什麼證據說有早中晚觀念?八卦分別代表了不同的事物,有自然界的,有人類社會界的,比如家庭成員。乾卦下面的這三個陽卦中,“震”是長子,“坎”是次子,“艮”小兒子。坤卦下面的三個陰卦中,“巽”為大女兒,“離”為二女兒,“兌”為三女兒。這些子女就是在不同時間出生的。八卦中的陰陽沒有明確的時間性,而早中晚三階段是時間性的。早中晚是三個,陰陽是兩個。三和二,用數學的方法組合,就是六個,再組成重卦,就是六十四個。由二到八,中間有個六。從二發展到三,中國古代的數就到此為止,以后都以象為主。
可見,《周易》的陰陽兩分,不是嚴格的對偶,不是相互排斥的,無法發展成邏輯學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因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后來的陰陽魚或太極圖之中。《周易》的陰陽二數,發展出三,沒有沿著兩分的原則向下發展。《老子》也背離了兩分,由數進入象術的領域。陰陽觀念是經驗的,沒有升華到思辨的高度。從另一方面看,《周易》的陰陽是運動的,可以互補,另外,早中晚的時間概念也是變化的、循環的,從而可以為歷史理性提供哲學基礎,即事物是“變”與“常”的統一,有一定規則可尋。另外,陰陽二者雖然有分別,但沒有互相排斥,沒有將不在場的舍去,二者都在場,沒有形成西方的在場形而上學,有利于中國歷史理性的形成和發展。歷史理性強調“常”與“變”,不僅考慮在場的因素,也考慮不在場的。可以說,西方文明中邏輯理性占主導和中國文明中歷史理性占主導,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
也許有好奇者會追問:為什麼中西的二分法會不同?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語言的不同有一定的影響。語言的特點在很大的程度上導致了邏輯的特點。語言和邏輯是緊密相關的,中西皆同。屬于印歐語系的希臘文有一個特點,即一些詞加上前綴a,就構成該詞的反義詞,從而產生一對意思相反的詞,正是兩分法的對偶性。比如:tomos是分割的意思,加上前綴a為atomos(英文的atom)構成分割的反義詞:不可分割,即原子。追究中西文化不同的原因,追到語言學特點,就算到源頭了。再往前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回答“什麼因素決定了中西文明起源時不同的語言特點”這樣的問題。
作者附言:本文原是2010年6月我在上海師范大學參加一個史學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2017至2018年間,大約有半年時間,陳寧博士每周三來我家討論學術。他根據錄音,整理成文,而且核實了相關資料,并對第一部分的前人觀點做了增補。這篇文章是我們共同勞動的成果,特此說明,并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謝!
①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靜庵文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頁。
②林語堂:《論東西思想法之不同》,《林語堂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174頁。
③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頁。
④張東蓀:《知識與文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99—101頁。
⑤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序論,第5—9頁。
來源: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352582.html

















